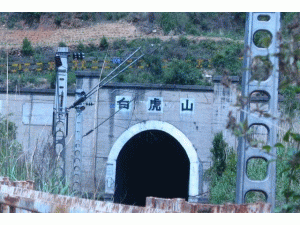遥 远 的 山 村
——谨以此文悼念李放安战友
五月的一天下午,突然收到西安战友果玉峰发来的一条短信:“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李放安死啦!”
“谁?李放安?”我问。
“咳!就是宣传队那个我们陕西剧团的啊!翻跟头的那个小孩。”
是他!我眼前蓦然浮现出一个形象:中等身材、大脸盘、牙的中间有点泛黄、一口地道的陕西关中口音的大孩子。
我陷入沉思。
那是我们部队到青海后的第三个年头,我们团演出队又从基层连队物色了一批新兵,其中有个孩子很会翻筋斗,就凭那一串跟头,他进被挑中了。刚进来时,应该还不满20吧。平时他活泼爱动,显得十分淳朴稚嫩,逗人喜欢,久之,在队里大家都亲切唤他“小李子”。
我和小李子的关系,与演出队的其他战友们不同,我们曾有过一段独立的交往——到一个小山村里给村民们做了两天的文艺辅导。那个情景,历历在目,至今难忘。
那年的7月,我和小李子一起下到三营八连体验生活。除了和连队战友们一起参加劳动,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连队的文艺骨干搞培训,并顺便帮助他们排几个节目。一天,我们正在连队的小礼堂排练,进来了两个面色黝黑的蒙古族青年,站在一边津津有味地观看,门外,栓着一黄一黑两匹蒙古马。一会,当我们歇息的时候,他们用生硬的汉语对我们说,他们村里要搞文艺,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帮助他们也搞搞文艺辅导。小李子激动地连声说“好哇好哇!”,我也很高兴——当兵快四年了,还从没有直接和当地的老百姓接触过呢!这可是军民团结的好事!给连里说了一声,我俩一人一个,在俩蒙古青年的帮助下,笨拙的爬上马鞍,坐在那俩蒙古青年的背后,抱着他们的腰。待我们坐稳,他们一甩马鞭“駕”——马儿蓦然起蹄,我们一个趔趄,向他们村驰去。
马儿载着我们,在草原上奔驰着。高原的蓝天像用水洗过似的,是那种令人陶醉的纯粹的深蓝,蓝天下的草原,犹如碧浪般涌动,各种不知名的花草,散发着一种像熟透了的苹果的芬芳。小李子在马上情不自禁地放开嗓门“噢——!”、“噢——!”地大喊,倾泻着年轻的激动。一会,马儿离开草原,进入了一条两边是黄褐色岩石的山沟,弯弯曲曲转过几个山坡,最后突然折进一条很深的山沟,在山沟的尽头,一转,眼前出现一个山凹,山凹的一边坡地上,不规则地散落着一些人家。房子,多数是用泥抹平屋顶的黄灰色的土坯房(青海老百姓普遍居住的那种典型房子),还有几间黑色的毡房,醒目地扎在村落的边缘。每个房子和毡房外面,有用土坯或者木头扎起的篱笆,那是圈养羊群的羊圈。村子中间,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几米宽的村道。正是中午饭的时候,各户黑色的烟筒里升起了袅袅炊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羊粪的鲜膻味。
刚走进村口,小李子就迫不及待地从马上蹦下来,这里瞧瞧,那里摸摸,满眼的新奇和惊喜。一群人,穿着各式民族服装,老老少少的,围了过来。他们可能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解放军到他们村,十分兴奋地上上下下打量我们。小李子热情地和他们打着招呼::“老乡们好啊”!并伸手和一些年轻汉子握握手。虽然他们在笑,但笑脸上却分明写满了“他在说什么”的疑问。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绛红脸膛的高大汉子,用较为标准的普通话和我们招呼。原来当时正好有一个县委工作队在这里,这位高大粗旷的汉子,就是工作队的成员。他是从甘肃来乌兰的汉族老师。自然他立刻成了我们的翻译。于是,我们和老乡的交流马上顺利起来了。随后,这位汉族老师一直陪伴着我们,给我们当和村民沟通的桥梁,直到我们离开。
中饭是在一个家境富裕的蒙古族村民家吃的,主人很客气,有手抓羊肉,还煮了滚烫的酥油茶。青海的手抓羊肉膻味不浓,有一股特别的香味,沾着佐料很好吃。酥油茶倒有种微微的鲜腥和酸味,一般我们部队的人不习惯。我以前曾经喝过,难受。但此刻主人盛情难却,只得忍着难受,一口一口地抿着,更多的时候是拼命地用小刀割羊肉吃。但意外的是小李子喝起来似乎很适应,用嘴吹吹上面的浮沫,“呼啦”一下,一碗就下去了。喝完了,递碗过去,又是一碗,喝的主人眉开眼笑。 主人一边劝我们多喝,一边还给我们介绍和夸赞酥油茶的好处,强身健体、冬暖夏凉什么的。
我们通过那位汉族老师,打听起了这个山村的情况。这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小山村,有蒙族、汉族、哈萨克族、藏族、还有回族,总共也就三十多户人家。村子农牧并存,既有种地的,也有放牧的。这回县里要在他们村办个什么点,想搞节目,所以把我们请来了。
饭后,我们开始给他们做文艺辅导。没有想到,人们居然对此有这巨大的兴趣和热情。除了年纪较大的老人外,中年以下的男女:大哥、大嫂、姑娘、小伙、孩子,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都参加了。在一块较为平坦的坡地上,高高低低地散站了一片,激动不已的叽叽喳喳,笑语渲然。
好不容易,我和小李子帮他们整好队,能够按照我们的口令做立正稍息的动作了。我要小李子先给大家表演一盘,小李子高兴地翻出一串漂亮的跟头,看得他们眼花缭乱,惊叹不已。然后我们开始做辅导。其实做辅导也就是最简单的舞台知识,怎样站啊,怎样放手出手啊,眼睛怎样看啊,脚步怎样走啊等。但就这么简单的,对于这些深山里的人们,还真的是一件难事。你先给他们做一个示范,他们一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百式百样的,令人忍俊不禁。孩子还好一些,尤其是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又特别的认真,一认真那胳膊腿就特别容易的发僵,有的时候,你还要使好大的劲给他们板正,就像上了锈的铁条一样硬是板不直。对他们说不要紧张嘛,他(她)就说我没有紧张啊,叫你哭笑不得。我们只得不断地给他们示范,不断为他们做矫正。小李子因为太投入,一会儿就弄的满头大汗了。他干脆把军帽抓下来,往裤子口袋里一塞,露出一个圆圆的娃娃头,这边那边地跑动着。整整一个下午,我们才完成了站姿和挥手的辅导。
晚饭后,村里举行了一个篝火聚会,欢迎工作队和我们俩。几跟粗大的整体树蔸被堆放在一起燃烧着,红红的火焰在欢快地跳跃,清冷寂静的山沟,顿时充满了温暖和热烈。一些孩子在跳着简单的圈圈舞,我们和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和老乡们聊天。一会,一个位蒙古族青年,赭色的脸膛,穿着马靴,站在火堆边,遥望着夜空,唱起了一只古老的蒙古族民歌。那是一首我们从没有听到过的歌曲。青年人那自然高亢、原生野性、又微微带些沙哑的嗓子,演绎着那悠扬、婉转、激越和低回交织的旋律,唱出了遥远、深邃和神秘的草原梦幻——是天边游荡的羊群;是草原上潺潺流淌的小溪;是牧民们转场时牛车的轱辘;是夕阳西下时磷光闪闪的湖泊;是那达慕骏马奔驰的鞭响;是毡房里热气腾腾的奶茶.......。一时间,没有了私语、没有了舞蹈、没有任何响动,时间静止了,只有青年的歌声在漆黑的夜空中飘荡.......。好久好久,我没有回过神来,当热烈的掌声打断我的遐想时,已经找不见那个青年了。后来我问了房东,才知道他是一个长年在草原上游动放牧、刚从很远的牧场临时回家的牧民。
晚上,村里特意安排我们到一户汉族村民家就宿。房东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大嫂,壮硕而端庄,也参加了我们今天的文艺辅导。她还在为下午的学习而兴奋,给我们演示了几个动作,问做的对不对。小李子也非常乐意地为她做了好新的几个舞台动作,并讲解了一些要领。我们趁机和她又聊了一会。她告诉我们,她说从甘肃的天水过来的,这边有亲戚。丈夫在城里做事,平时就一人在家,没什么客人的。今天解放军来了,她特别的高兴。特意让出来她自己的卧室给我们就寝。油灯在跳跃,宽大的土炕烧的很热,室内充满温暖。等房东大嫂一走,小李子在炕上立马做了一个倒立,在炕上用手转来转去。钻进被窝时,他不断地攒着嘴,连连说到:“好舒服,好舒服!”
第二天,我们依然给他们搞辅导,但感觉顺畅了许多。辅导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在舞台上行走;如何亮相;如何使用面部表情;再加上一些流行的藏族和蒙族的典型动作。许是人们的业余生活过于贫乏,这样的活动让他们感到新鲜,人们高涨的学习热情令我们吃惊。不时有大嫂、姑娘、孩子这边招手那边喊叫:“哎,解放军,我做的对不对?”;“快过来快过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快结束时,我们让人们将全部的学习内容演练了几遍,还真的像一会事了。工作队的几位同志站在一边观摩,开心不已,笑逐颜开。
下午四点,我们谢绝了工作队和人们的挽留,回连队了。高原上的气候是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阳光万里,蓦然之间,乌云密布,变成了一副要“哭”的样子。我们着急了,没有等专门送我们回去的配好了马鞍的马匹回来(到山上去吃草),让两个青年拉来了两匹光背的牧马,像来时那样,抱着他们的后腰就往回跑了。马儿飞奔着,小李子依然很兴奋,在马背上高声的对外喊道:“老刘,嘿,真过瘾哦”!。过瘾是过瘾,但却是难受极了。骑在光秃秃的马背上非常颠簸,比行走在坎坷山道的吉普车的颠簸还厉害的多,加上没鞍子人又紧张,动作僵硬,感觉人都被颠散架了。到了连队,小李子似乎没什么事,跳下马就开始活蹦乱跳的。但我却惨了,两只腿已经僵直得迈不开步子,而且,我的尾椎骨那地方似已经磨破,沾乎乎的,疼痛难耐.......。
...................。
往事,如烟一样飘散于时空的远方。我是先离开部队的,后来小李子在部队呆了好久,回家又经历了哪些人生的风雨起落,因为没有联系,我无从知晓了。没想到今天当我刚知道他的行踪,竟然是他离开我们的时候,真是世事难料啊。在他健在的时候,他是否曾经想到过我们一起度过的这段特殊的人生一瞬,想到那个偏远山村呢?我想,小李子,你我拥有了我们的同辈人没有经历过的一段特殊而美好的时光,虽然极其短暂,但,它曾是我们共同享有的一个精彩的生命片断,是我们俩独占的人生财富。也许,在那无限广漠的天国,你携带着它,会邂逅到那山村的一些朋友......。我相信,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再次相逢,我一定邀你一起,重回那个遥远的山村........。
小李子,你能听吗?
【值“八一”来临,追忆部队生活,谨撰此小文,纪念战友】01.7.31



 河边草
河边草 305239464
305239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