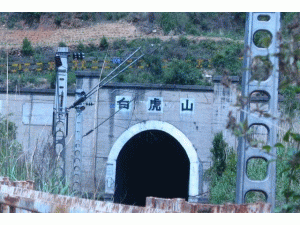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每当我读到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水调歌头》中的这几句时便想起在那军旅生涯的15年里,一次次与我的老母亲离别的情景。
记得第一次分别是在1968年3月7日。那一天,我穿上了崭新的绿军装,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晚饭后,班长悄悄告诉我,夜里就出发了,快回家看看。我急忙借了一辆自行车,风驰电掣般朝家骑去。
夜幕低垂,行人稀少,路灯眨着眼睛静静地看着我。我无意欣赏古城的夜景,心里想着此时老母亲正在干什么?
我们兄弟7人,兄长都已成家,只有我和年逾花甲的老母亲相依为命,我走后家中就只剩她只身一人了。
推开家门,看见母亲已吃完饭正在捡碗。饭盆里装着不少馒头,足够老人家吃几天的。我一只脚刚迈进门坎,就气喘嘘嘘地说:妈,今晚我就走了,请半小时假来看看您。老人家放下手中的碗筷,转过身来:别惦记,快走吧,别过了时间。边说边把我推出门外。
我转身骑车便往回走。路灯依然眨着眼睛看着我,而我脑海中却是一片空白。
子夜,列车徐徐开动。我们挤在车窗前往外看,万家灯火的锦城渐渐远去,心里真不是滋味,心想不知何时才能回来看看生我养我的家乡,看看我那年迈的老母亲,往事便一下子浮现在眼前。
在家里我最小,母亲也最疼爱我。虽然我已经长大了,但在她眼里始终是个孩子,不让我离开半步。1966年6月,高中毕业后,我被录取到法国留学,那一批全市才只有4人。遇到这样好事,家长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是,当老师来家征求她意见时,她却说:不同意,我不放心。她的回答,竟使老师目瞪口呆。老师做了半天工作,老人家才勉强点了点头。后来文化大革#开始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母亲反而像卸掉了沉重的包袱,露出了笑脸。
接受上次教顺,我报名参军唯独没告诉母亲,直到入伍通知书发了,瞒不下去了,才乘老人家高兴时说:妈,我有件事想跟您说,您可别生气。妈笑着说:说吧,妈不生气。妈,我参军了,怕您不同意,事先没告诉您。妈听了我的话,笑容没有了,沉默了好长时间说:去吧,这是好事,妈同意。没有国,哪有家?
老人家经历了几个朝代,伪满时期当过亡国奴。为了生存,带着一家人逃过荒。饱经沧桑的她深深懂得先有国后有家的道理。
参军后,哥哥来信讲,母亲一个人在那间小屋里住了半年多。六嫂生小孩,需要人照顾,加上不放心老人,才把母亲劝到六哥家。母亲虽然走了,房子却没交,宁愿每月交房租,目的是等我退伍好母子居住。直到后来我被长期留队,母亲才把房子让给了别人。
当战士时四年一次探亲假,提干后一年一次。那时分别虽然也不是滋味,但也没什么,母亲从来不送我。
由于岁月的流逝,母亲的白发一次比一次多,离别时老人难受的心情也一次比一次重,这种感情上的微妙变化,只有做儿子的我心里最清楚。但是,部队铁的纪律我不能为了母子之情超期归队。没有办法,我常常把假期说短。在家的日子,时间过得特别快,转眼就要到期了,老人家脸上的笑容没有了,一声也不吭。到了我说归队那天,妈看我没走,就催我:回家看看就行了,别误了假期,当我告诉她还可以呆几天时,老人笑了。
母亲在家里养了几只鸡,下的鸡蛋平时舍不得吃,都攒起来留我探家时吃。我告诉她部队生活很好,什么都不缺,鸡蛋留着自己吃吧。她说,部队是部队的,家是家的。我理解老人的心情,便大口大口地吃,她在一旁看着,那样子真比她自己吃还舒心。
我每次探家,从不告诉家,免得让母亲受翘首盼望之苦。有一次,我早上5点多到家敲门,六哥从炕上爬起来惊喜地说:妈,好像顽石回来了,妈说,别白话,当我真的站在老人家面前时,她笑得那样开心。
母亲一生操劳,父亲是个老实的庄稼人,在世时只会干活,母亲成了一家人的主心骨。生活的磨练使母亲养成了刚强的性格,每次离别从来不哭。别人问时她说:孩子到部队是好事,又不是进监狱,有啥哭的,哭天抹泪只能让孩子心里不静。
记得最后一次探家是在1978年,老人家的头发全白了,由于患了几个月病,身体也大不如前。那一次,老人家真舍不得我离开,在探家的日子里,与我寸步不离,我理解老人的心情,也尽量在家陪她。
要归队了,哥嫂说:顽石要走了,妈不送送?妈说:不送,话音未落,却先出了屋。哥哥问:妈您干啥去?妈说:我到商店看看。哥嫂推着自行车陪我出了家属院,上了公路。当我回头看时,发现老母亲站在商店门口,痴痴望着我,望着我渐渐地离去。看到老母亲那难舍难离的样子,我的心颤抖了,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



 河边草
河边草 305239464
305239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