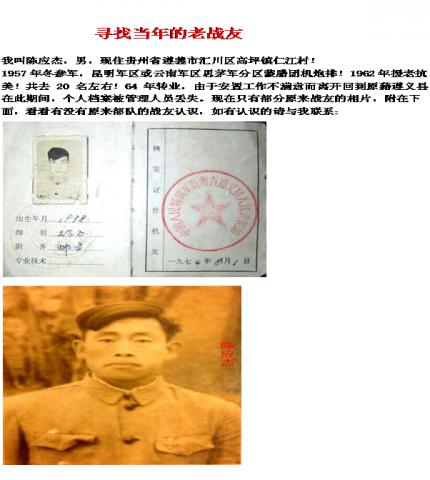铁道兵史诗《远去的背影》出版遭遇尴尬
作者无奈寻求帮助
我叫刘金忠,是1970年兵,刚当兵时在铁14师66团17连,当过文书、副班长,在连队不到一年时间,调师部当警卫员,1971年调铁道兵文工团当通信员、文书、创作员,1977年调到铁9师当干事,1982年转业到焦作日报社工作。
我在2008年创作了一部长诗,定名为《远去的背影》,2000余行,此诗全景式地再现了铁道兵从组建到撤销35年的光辉历程,可作为铁道兵的一部史诗,结稿后,曾在网上搞了一场近三个小时的专题朗诵晚会,受到光大铁道兵家园的交口称赞,参加晚会的战友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因为,这部长诗说出了我们所有当过铁道兵的人的心里话。我作为铁道兵培养出来的诗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来做这件事,一是我在部队时就曾经常在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作品,当时写的也都是反映铁道兵生活的诗歌,在铁道兵的诗人里,我虽算不上最好的诗人,但也算得上有一定份量的诗人,加上我在连队、团、师、兵部机关都干过,掌握的素材很多,我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二是我和许多战友一样,对铁道兵怀有很深的感情,特别是在铁道兵撤销后,深感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这也是我写这部长诗的一种动力。诗写出后,我很想把它出版了,让更多的战友能看到,一起怀念当初的铁道兵生活,怀念我们曾经流过血汗的那段难忘的岁月。为此,我还请广东的战友帮我找当时还在世的原铁道兵政委宋维栻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但我是个清贫的工薪族,每月3000元的工资,如自己出版这部长诗,一年工资还不够,确实也是不小的经济压力。因此,我希望能得到帮助,把这部长诗出版,我也在有生之年为我们铁道兵做一件有益的事。
就我本人平日交往的战友中,还没有很有钱的老板,我只好想到原铁道兵单位、现在的中铁建去试一试,去年元旦前,原铁9师的部分宣传部门的战友在北京中铁19局聚会,我去参加了,为此我花了几百元钱把这部长诗印了100本,作为打印稿带了去,我想借此次机会和局领导说说这件事,看看他们会不会帮助把书出版了,但领导身边的人告诉我,最好不要张这个口,领导们都在忙项目的事,心思不会放这上面。为了不影响聚会的气氛,我听从了他的劝告,不能自讨没趣,只是把印好的书稿送领导们各一本。
当时我又想去中铁建机关问问,可我不认识那里的领导,就经原中铁15局的书记王炳祥介绍,找到中铁建的副书记霍金贵,他现在已退二线了,抓铁道兵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他对我很客气,我把来意讲了,把书稿送给他一本,他说,我不懂诗,但你这种对铁道兵的感情我很理解,筹建铁道兵纪念馆是有些经费,但比原来预算压掉了三分之二,也很紧张,他问我出版这本书要多少钱。我说,如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钱要多些,估计要十万八万的,这样的书最好是能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他说,按说钱也不算多,也就一餐饭的钱,但我退下来了,说话也不管用了,但你这本书稿可以放在建成后的铁道兵纪念馆展出。他的爱莫能助我也能理解,但也不甘心,就请他给下面一些局里说说,看有没有哪个局的领导能帮助一下。他说,他可以尽量去说说,但不敢打保票。
我怀着一颗失落的心离开了北京,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很纠结,感到无助,感到尴尬,也为我们铁道兵而尴尬,试想,如果将来铁道兵纪念馆开馆,作为铁道兵改工后的中铁建,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的《远去的背影》放在纪念馆的展柜里,这对年产值几千个亿的大单位来说,是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呢?显然,他们都把出版这本书当成了我个人的事,而没有看作整个铁道兵的事,作为一个中铁建的下属局可以认为,你写的是全铁道兵的事,让我出钱来出版这本书,心里总是不自在,而中铁建也可以这样认为,你写的是前铁道兵的事,与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假如再过几年,中铁建里面原来当过铁道兵的人都退下来了,还会有谁去管我们铁道兵的这些事呢?
我也深深感到悲哀,我一直对铁道兵怀有很深的感情,很多次在梦里都梦到当年的铁道兵生活和那些战友,我是在以自己仅有的能力来歌颂和怀念我们铁道兵,所以我写出了这部长诗,但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我自己的事,其实,我不为名,也不为利,要说为出名,我大可不必用这本书出名,当年在部队时,我在全军也算是挂上号的作家了,我的作品已收入《新中国50年诗选》、《解放军文艺30年诗选》、《20世纪汉语诗选》,也在全国诗歌大赛中几次获奖,用不着利用这一本书来出名,至于利,就更谈不上,出这本书我可以分文不取,只是为了更多的铁道兵家园能看到这样一本书,别无他求。
在几经碰壁后,我决定在网上说出我的这些心里话,希望有经济能力或者认识有经济能力的战友的老铁们,希望各省市的铁道兵家园协会的战友们,仔细看一看我的这段文字,如能提供支持,将这本书出版了,我也就可以宽心了,这也是为我们所有的铁道兵家园们做一件善事。如果求助不到,我也只好将这部长诗放在我的博客里永久封存了。
谢谢战友们关注此文。



 河边草
河边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