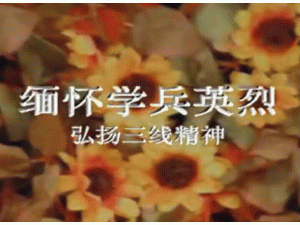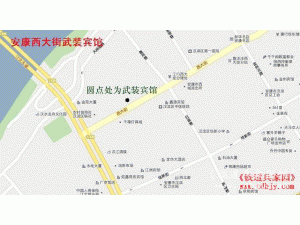|
[原创怀念紫阳:高滩寻梦 金秋时节,我携老伴来到高滩。从武汉到高滩行程近八百公里,一路上,我不时在问自己:这个贫困的巴山小镇,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这些老兵魂牵梦萦? 中午十一点十分列车稳稳地停在高滩车站。算起来,6065次车从安康出发,行驶二个小时就到了这里。想了想,当初进山的时候,我们从宁陕县城关翻山越岭到高滩镇,走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尽管列车这样行驶还不算是正点,我仍然十分开心:火车真是个好东西。 天下着雨,还是满地石头和稀泥,高滩车站下山的路十分难走。好不容易搀扶着老伴战战兢兢地下了车站那个没有台阶的坡坡,越过泥巴凼子,乘坐桥下候客的五元小巴向镇里驶去。眼看就要到高滩镇了,听着发动机在轰轰轰,我的心也在咚咚咚。 象久别的游子回到故乡,我的眼睛已经不够用。离开这里已经三十五年,眼前的景物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陌生。远处,襄渝铁路复线和安毛高速在修建,雨中的高滩显得十分宁静。放眼望去,沿任河岸边向山坡延伸修建的房屋错落有致,楼房明显比以前多,房屋的质量也不差,有些楼房还十分讲究。矮滩隧道口两边昔日荒凉的山坡也修建了石瓦屋,参差不一地分布在坡地上。刚进山时修的那条公路两旁,现在已是商铺林立,我还误以为是镇上的那条老街。呵,这个古老的小镇已经是一座正在兴起的开放小镇,充满着市场经济的气息了。 象在百度上搜索一样,我留心着街上的行人,很想碰到或者辨认出以前熟悉的朋友。东张西望,竟然全是陌生的面孔。想当年,我们只要到镇上一走,总会遇见许多可打招呼的熟人啊。高滩变了,变得我都找不到重回营区的路。只有对岸那象海豚嘴样的小山包,静静地卧在任河和绕溪河交汇的地方,默默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和小镇的变迁。 三十多年了,现在的高滩还称不上富裕,但在我的心目中,高滩却是那样的美丽。你看,任河的碧水、小屋的石瓦、葱绿的青山、桂宏溪上那仿佛挂在天上的彩虹桥,构成了一副小镇独有的美丽画卷。这样美的景色哪里去找啊,怪不得美术学院的学生常要到这里来写生。 望着熟悉的山山水水,记忆的火柴擦亮,过去的那些模糊的东西瞬间变得清晰起来。七十年代初的高滩贫穷、落后, 全镇唯一的一条石板街上,行走的人们背着背篓,脸露菜色、衣着破旧。地处深山的有些贫困人家,一套衣服外出时轮流穿,有的人身上甚至绑着棕皮御寒。镇上仅有一家算是称作商店往往是这也没得那也没得的供销社。破旧、低矮的房屋分布在任河岸边,一些居民做饭时炉子口还放着几个鸡蛋大的石块,后来才知道是烧石灰。 高滩交通不便,所用的生活物资都是人背肩扛。公路没通车的时候,我们从紫阳挑着装备、物资经瓦房店、芭蕉口到高滩,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沿途看到那些手拿丁字架负重运输的高滩百姓,停下歇息时的那声长吼,至今还在耳边缭绕。公路开通,汽车进山了,广城、李家沟、双柳、茶店子一带的村民们成群结队到镇上看汽车,热闹的场面象过年一样。由于没见过汽车,村民们提的问题千奇百怪,战士们听了,都发出善意的笑声。部队以此创作的八个老头看汽车,还上了宣传队的节目单。 往事历历,恍如发生在昨天。眼下,看着高滩镇的商铺物资丰富、行人衣着整洁、公路上当地村民营运的巴士来往穿梭,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今非昔比,感到特别欣慰。 沿着桂宏溪往里走,是我们连队的驻地。曾建有干打垒房屋十几栋,盖的也是石瓦。那是我们连湖南长沙藉蔡指导员带领战士和民工修建起来的。如今,熟悉并住过的指挥所、连部等房屋都已经消失,原址上建起了高滩小学和整洁的民居,溪也显得窄小了。站在高滩小学的操场,望着清清的流水,听着这熟悉的水声,心情似溪水在奔流。这里,曾是我们度过青春岁月,流淌着我们的汗水、泪水、血水并留下美好记忆的地方。时光流逝,当年部队从战地越南回国来这里,我们都只是十八、九岁的青年,今天,却已经两鬓染霜。 在雨中,老伴陪着我走走、停停、看看,努力寻找当年的痕迹:修建房屋时炸翻的巨石还在;我在溪对面山崖石壁上安放过滤桶的凹凸台阶还在;溪边生长的鸭拓草、墨旱莲依然在开花;蔡指导员在动员会上发出尽快打通矮滩子隧道,不仅要让高滩人民坐汽车,更要让高滩人民坐火车誓言的场地也还在,睹物思人,却再也看不到战友们落雪时在溪里洗澡、打闹的情景,再也听不到民兵连驻地夏夜时常吹响的阵阵唢呐声。 桂宏溪边,矮滩洞旁,曾经发生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啊。隧道口的顶端和旁边,分别刻着为人民服务主席手迹字体和矮滩隧道四个魏体大字,字体木模是湖北宜都的一名战士花了三天时间用手工制成。离隧道口不远的上方,七一年因雨雪,片石发生松动,滑落下来砸断正在勘探的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分配来部队的技术员左腿,后伤重不幸牺牲;上导坑掘进风枪手在洞口被钢拱架砸中头部当即身亡;横洞贯通,一名江西籍军代表和三名民兵期盼隧道对接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不幸遇难。那一次,放的是整整二十炮。负责爆破的河北遵化籍六班长在指挥所数炮,二十炮数完,电话也响了:横洞发生伤亡。我们急忙跑去现场,那个场面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当初公路没通,物资全靠人挑肩扛,我们同去紫阳挑装备的一位江西于都籍战士从紫阳回高滩,为赶回连队,不顾水流湍急,过竹瓜溪时不慎被冲进任河,救他的一位广东战友也负伤;我们营一位通讯员拉纤,为了好使劲,大背着纤绳,急流汹涌,强大的冲击力使船只象脱缰野马,同伴们单臂纤绳脱肩,他却被逆流而下的船只带下水,一个英俊小伙子,把自己生命融入了滚滚任河。 民兵连队比部队还要苦。打林家隧道的时候,有位家庭困难、子女多的民兵,坑道作业劳动量大,他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馒头积攒起来,定期让孩子拿回去。那天早晨孩子兴高采烈提着馒头回家,晚上,他却因在隧道掌子面上受伤,不幸身亡。毛坝山体大塌方,有多少民兵兄弟姊妹遇难?这些场景令我们悲痛不已、心酸不已。 在网络上,时常可以看到铁道兵部队和西安学生兵发表的描述修建襄渝铁路艰辛的文章、诗歌和视频,反映紫阳县民兵师艰苦卓绝斗争的文章却很少。其实,紫阳县人民为这条铁路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军队、学生兵一样,是应该载入紫阳县发展的历史史册的。 这条连接湖北、陕西、四川、重庆四省、市的钢铁大动脉,是大打人民战争修建起来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装备差,技术落后,物资缺乏,靠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敢、牺牲精神。那时,人们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要贵重,部队如此,地方也是这样。西安学生兵、当地民兵和部队战士一样,哪里危险冲向哪里,极少有人叫苦叫累,军民都承受了很大的牺牲。可以说,这条路,是军民的血肉铸就。真可谓一寸隧洞一寸血,十万民众十万兵。 年龄大了,过去的事总是忘不了,现在的事老是记不住。讲多了,怕是讨人嫌,在家子女们也是这样说过我。咱说点别的,说说在街上遇见的普通高滩人。 如果用较为精练的语言来评价高滩人,那就是勇敢、坚韧、善良、好客。 刚来陕南,常说紫阳十八怪,住得久了,晓得怪有怪的道理,我们慢慢被同化,也成了怪。今天走在小镇街道上,听着那久违了的当地话,看着那熟悉的背篓、核桃,感到紫阳话听着就亲切,高潍人看着就温暖。我和老伴到离任河公路桥不远的一家夫妻开的小面馆吃面,也顺便避避雨,端庄秀丽的老板娘和在面馆就餐的李姓顾客知道我是当年的老兵,热情有加。回忆、述说当年的情景,介绍三十五年来高滩的发展、变化,相谈甚欢。老板娘不仅酸菜面做得味道鲜美,人也贤淑,知道我们要回紫阳县,见细雨绵绵,道路泥泞,主动帮我们拦车,还帮老伴把行李送到车上,让我们十分感动。 在崎岖的上山小路上,看到高滩小学建在山腰,坡陡路窄,老伴直叹息:孩子们上学要爬这样高的山,遭孽啊(武汉地方话,即:受苦、可怜,包含同情的意思)。她哪里知道,当年高滩小学学生的学习条件,不知道要比这艰苦多少倍呀。我和老伴走走停停、指指点点介绍着连队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山路上,一个中年男子手里提着豆腐,跟在我们身后,静静听着我和老伴说话,始终不超越我们,看他的微笑和眼神,这是一个朴实、善良的高滩人。经交谈,知道他姓任,小我三岁,家就扎在高滩小学附近。那时年龄小,没参加襄渝铁路的修建,但对当时发生的事如数家珍,还记得我们当年的洞九部队(铁二师九团),听他这样一说,我非常欣慰。从他那里,我知道桂宏溪发生的变化和部队营房的变迁,也了解高滩人民对当年铁道兵的一片深情。雨中,他一直陪着我们,直到经过他的家,真诚地要我们到他家去坐一坐。下山经过他家时,他还站在院子门口,高声邀请我们到他家喝茶、休息。令我感动不已。我和他素昧平生,他却象老朋友一样对我,高滩人是多么讲礼性啊。其实,我很想到他家喝口茶,因为他扎的地方,正是我们连队当年的驻地。看到老伴催着要走,只好婉言谢绝任兄弟的盛情。 我知道老伴的心思,她为什么急于下山:是怕赶不上回紫阳县的汽车。天下着雨,担心第二天乘火车再走高滩火车站的那个坡坡。我也纳闷,一个车站,是一个地方的脸面,人们一踏上这块土地,往往从车站衡量经济发展和政府关心、重视民生的程度。高滩火车站出站的坡坡太危险,坡陡路滑,坡下就是汽车行驶的公路,如果旅客不慎摔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高滩镇是不富裕,但是整理这个坡坡让它至少安全些是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可以解决的呀。如果高滩火车站建设才三、五年,车站设施不全倒可理解,但高滩站建于1972年,襄渝铁路通车已经三十五年,那个山坡不到二十五米,就是每年挖一个凼子,垫几块石头,旅客出站下山也不至于提心吊胆,害怕跌到公路上。高滩站每年发送旅客2万多人,三十五年来,旅客都是这样出站的吗?即使是一条临时路,也要为旅客的安全着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不是一句空话,有着非常具体的内容。政府以百姓为本,学校以师生为本,车站以旅客为本。难道修建一条简易、安全的下山路,比当年紫阳、高滩人民打隧道、架桥梁还难?山区人民可以忍受,但镇政府和车站不能这样心安理得。这种状况,不知道是高滩镇政府不思进取还是高滩火车站对旅客安全的忽视、冷漠。我盼望有这样一份承诺:让高滩火车站有一个安全的下山小道,是镇政府提出的O九年为民众办的十件实事之一,这也是我的一个梦。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重走高滩的路,再来回忆陕南那些年艰苦奋斗的青春岁月,心中那份难掩的情怀,已经不是这个吃着蛋挞、疯狂Party的新时代人所理解与分享的。当我坐上紫阳开往安康的火车,行驶在这条我们亲手修建的铁路上的时候,真正感受到,辛勤付出之后,才能享受幸福,才会珍惜。看到车厢里从紫阳出行的少男少女们青春靓丽,兴致勃勃地在一起高谈阔论,心里那份羡慕和满足,只有我自己才清楚。我想,正是这条铁路线,让无数紫阳、高滩的优秀儿女走出深山,并从这条路上走向全国、奔向世界,我们作为这条铁路上的一颗小道钉、一粒小石头,委实感到欣慰和快乐。 |



 河边草
河边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