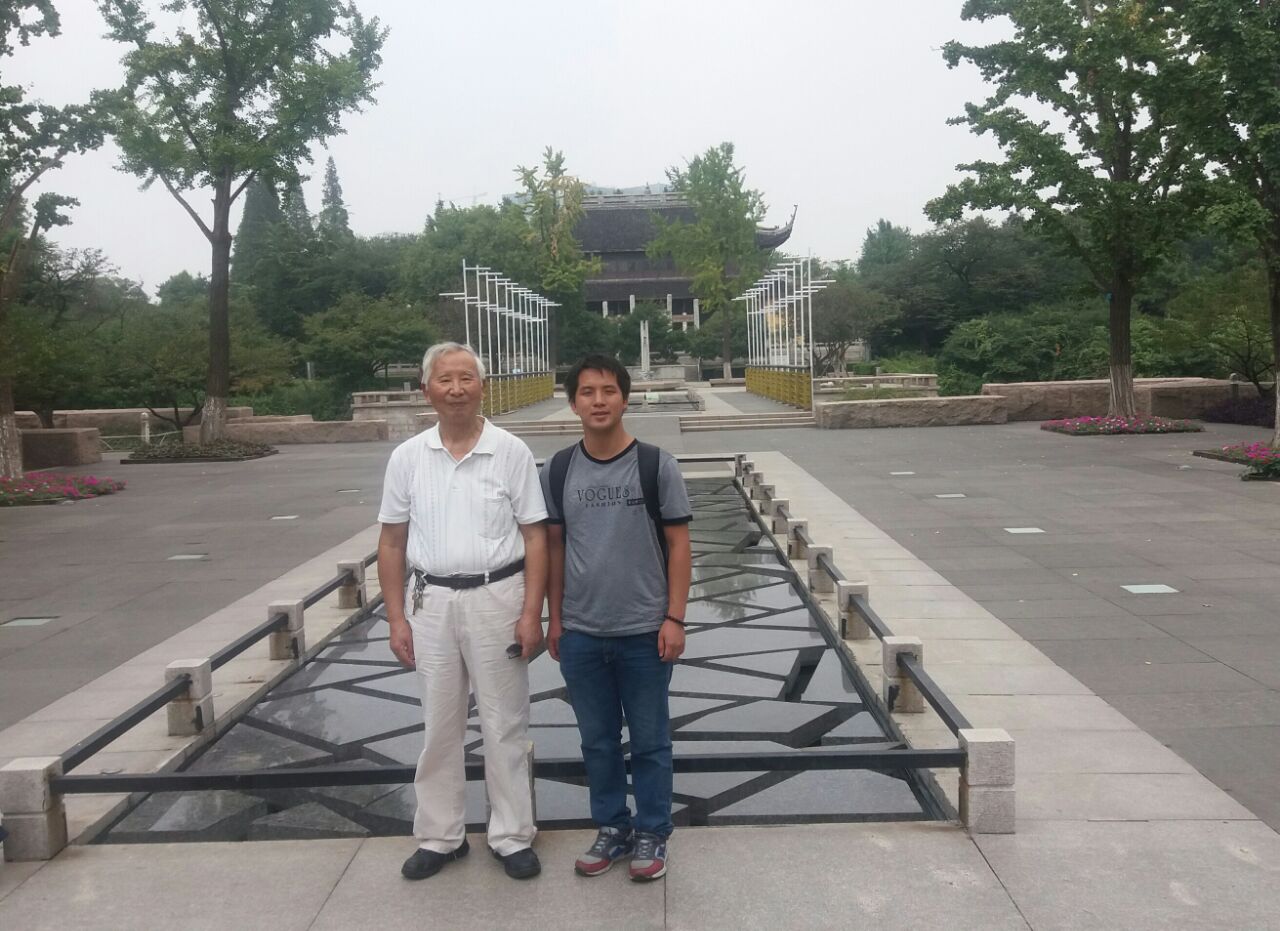每个人都有值得回忆的往事,那尘封的历史是一曲曲动人的的乐章,奏响着时代的最强音。
共和国诞生,是我出生前震惊世界的大事: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天安门广场那震天动地的礼炮、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军民欢呼万岁的口号声,标志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9月10月,我出生在西安市的一个美国人办的医院。我追随着共和国走过了五十九个春秋,经历了风风雨雨,在共和国怀抱中逐步成长,我所经历房屋的变化,反映了共和国房屋变迁的一个缩影。
当我睁开双眼观看世界时,正值建国初期。中国满目创伤,百业待兴。此时的美国政府与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正挑起朝鲜战争,并把战火烧向中国边境。
1951年2月中旬,当兵的爸爸黄振荣,带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三师,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跨过鸭绿江,在朝鲜大同江桥沿线三百多公里地带,担负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筑起了打不跨、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由于父母都是入朝军人,刚五个月的我随部队入朝,住在了三师指挥部用闷罐车改装的列车中,车厢就是我们的家。我幼年车厢的家在战争中渡过,美机轰炸列车的炮火,成为我睡眠的摧眠曲。
邻近的朝鲜阿妈妮茅草屋,是我经常玩耍的地方…。
至到有一天,很多的阿妈妮围在车窗外泪流满面,手中挥动朝中支谊万岁的小旗,随着列车奔跑哭啼,我也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伤感?
懂事后听妈妈说,才知道那是志愿军回国时,朝鲜阿妈妮真情的流露。
爸妈回国后,我们家告别了车厢家的生活,家在北京市交道口铁道兵军营中安顿下来。
1955年初冬,爸妈接到王震司令员征服北大荒的命令,我们全家从首都北京来到虎林县,暂时住在日本鬼子留下的西大岗兵营中。
爸爸的任务是勘察完达山北亘古荒原。
1956年3月,迊着滿天的飞雪,爸爸黄振荣率领四个老铁兵,从虎林经密山到宝清。在宝清县委的支持下,由一名姓孙的老猎手当向导,带着枪支、弹药、军用地图,乘着一个马爬犁,驰向了宝清境东、完达山北千里雪原。他们风餐露宿七昼夜,从杨大房到朝鲜屯、从大河镇到长林岛,多次击退野狼的袭击,摸清了完北荒原有三百多万亩可耕荒地,随即向北京铁道兵总部发出请大军北上的电报…。
我妈妈赵英华帯着我和妹妹黄鲜民,随着先头部队挺进荒原,先是乘车,走着、走着道路没了,部队徒步行军。我和妹妹是趴在老铁兵叔叔背上进入荒原的,成为完达山北第一户北大荒随军儿童。
当时的农场是一片荒原,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铁兵在爸爸军用地图上标写“曙光镇”的荒草地段上,搭起了马架子。其中一栋成为我们童年在北大荒的第一个家,茅草堆成的地铺成为我们睡覚的床。
随着天气转暖,铁兵又相继盖起了拉合辩的草房。我们有幸成为第二个家的小主人,住上了土坯火炕。
1956年8月,随着铁兵大部队的进驻,铁道兵农垦局八五二农场职工子弟小学正式成立,开始头一次召生。6岁半的我,有幸成为农场第一批一年级小学生。
记得教室就在蓝天大地之中。课堂前面挂一黑板,用两个树杆支撑。课桌腿、坐位腿由土坯块垫起,桌面、櫈面就是长条木板组成,我们的小书包放在桌面上…。
记得当时小学老师,是部队转业来的女老师胡佩文。第一堂课上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老铁兵当年踏荒、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收获,近二十万亩荒地苏醒了,那广阔无垠的田野成为我们戏耍的天地。
1957年,王震司令员从多种地、多打粮的宏伟目标出发,把目光投向十二里外的南横林子。在爸爸等老红军的陪同下,王震把一把板斧砍入一颗白桦树中,发出命令:“腾出曙光镇种地,场部就建在南横林子这里…”。
新场部建成搬家以后,按照农场规划,我们有了新的校舍,教室墙壁是土坯叠成的,顶棚是柳条树枝,房顶是茅草苫顶。坐在明亮的课堂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随着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的到来,我们老师可谓人才济济,如余朝阳、桑良楣夫妇、孙善勇、寥继光,他(她)们参军前都是知识分子、大学生或体育教官,在部队担任将、校班的老师,当然也有随军家属,经问有位兰玉梅老师竞是印尼华侨。还有大学毕业随夫而来的赵木兰…。
这些老师在简陋的课堂,给我们讲理伦、讲数学、讲地理、讲化学、教俄语…,使我们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
这时上海市木工也到农场,成立了场直木材厂。老师傅们给我们做了标准学生用的桌、椅,从此我们告别了长条木板桌、椅,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这时,铁道兵农垦局八五二农场职工子弟小学,正式更名为八五二农场南横林子小学,后来了又有了南横林子中学。
劳动课是我们必修课:食堂菜园蔬菜是我们种的,学校厕所是我们修的,秋天教室外墙的黄泥是我们抹的,草屋冬季取暖的柴火,是老师带我们上山用爬犁拉的…。
也是在1958年,解放军总政组团来农场慰问转业官兵,那时的子弟校还有一栋木刻楞教室。在门外慰问团和我们小学生共唱歌曲,军中记者拍下了珍贵的照片:穿海军服的我,还侧着头唱呢;还有大妹黄鲜民端碗黄豆种,供一铁兵种豆的场面,收录在中央电影制片厂制作的“英堆战胜北大荒”的记录片中。可以说我们的童年在收获中成长。
我们家的住房也有了改观,农场盖起了五栋木房,是给爸爸三个老红军场领导住的,其它二栋一个是留给王震司令员来住的,一个是给当时戴右派帽子大诗人艾青住的,王震将军生前19次来农场,15次住在此木屋。
这木屋立柱是松木,做的墙内外用松木板咬缝,中间用锯沫填实,房顶是茅草盖顶,有着欧洲建筑风格。
爸爸等几位场领导,就在这几栋木屋中,调动了二万二干多转业官兵,三年开荒76万亩荒地,为共和国打下了粮食,受到朱德委员长的称赞和表杨。
1962年,在我家小木屋左侧,来农场视察的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大将、王震将军和爸爸等四位老红军合影留念,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爸爸成为走资派遭到批斗,蒙冤去世。我家的木屋成为批判的场所,屋内挂满了大字报,木屋外木板墙上,用墨汁写满了火烧、炮轰、打倒爸爸的大字,还用红色在爸爸名字上打上叉,久久留在过往行人的目光中…。
学校也成为动乱之地,学校的桌椅,被武斗的学生折的断胳膊少腿。教室的门窗也被砸的面目全非,学校部队来的老师家庭出身大都不好,多是大资本家或大地主出身,他(她)们遭到不同程度的批斗。学饺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取带的是高音喇叭震耳的造**言论…。
1969年5月15日,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到兵团最基层连队:二十团六营六连参加了工作。
为了修水利,我冬天住过地窝;建设钢铁厂,我也曾住过帐蓬。几十个人住一起。冬天油桶改装炉子烧劈柴,一天到晚室内,烟气腾腾,被褥有时捏得出水珠,最冷得三九天,需带棉帽子入睡…。
针对当时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错误口号,李先念在一次国家会议上说道:“建设兵团如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生产滑坡了,住房建筑停顿了,房屋破旧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农场粮食产量得到了提高,居民生活改善了。我家也告别了居住20多年、己四处漏风的木屋,住进了红砖做墙、石棉板做顶的砖瓦房,取暖用上了土暖气。
1985年,爸爸黄振荣的冤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王震副主任请示下,邓小平、杨尚昆圈批下,中央军委下发了给爸爸平反昭雪的决定,我们家族终于获得政冶上的新生。
如今我们家和垦区农场的干部、职工一样,住上了有集中供热,带卫生间的楼房。
現在很多农场楼房成群,别墅成片,住宅面积成为城里人渴望不渴及的梦想,而学校绿色成荫,楼房耸立,变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乐园。
我59岁的风雨人生,随着共和国的步伐前进:随父母从车厢的家到兵营,从首都北京的家到北大荒的家,经历过多次房屋的变化,使我深深悟性到,房屋越住越舒适,是共和国国力提高的象征。国富民也富,国强民也强,这一切是和先辈艰苦创业永远分不开的。
黄黎
2009.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