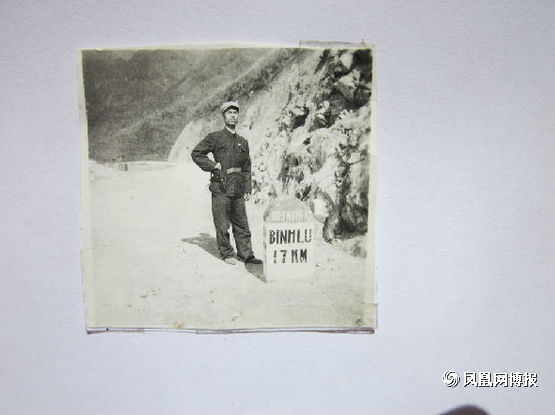三 磨滩巡礼
现在,我再回头叙述一下我们的住所。
我们铁道兵是专门修建铁路的,是一支不停流动的部队。因此,不像别的部队那样有固定的营房。铁路修到那里,我们就把营房“扎”到那里。如果当地老百姓有合适的空房子,我们就借用来当营房,如果没有这种机遇,便只好自己立帐篷当营房了。
这一次,营部驻扎的房子,正是借用公社的办公房。这个公社叫“工农兵公社”。很明显,这个革命化的名字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一片大改名的浪潮中产生的。它原来的名字叫“磨滩公社”。这也是当地老百姓所熟悉、所认可的名字。
公社办公房是一幢南北走向的单层的大瓦房。大瓦房中间沿屋脊方向是一堵砖墙,把房子分成互不相通的东西两部分。每一部分又分隔成许多小房子。我们营部借了西边这一排。从南端数起,第一间房子是炊事班,第二间是膳司、管理员,第三间是技术组,第四间是营领导,第五间是会议室,第六间是电话总机房,第七间是通信班,除第五间会议室外,每一间都像技术组一样,又是卧室,又是办公室。接着一间是公社的修理车间,从窗口看,里面有一台小机床,还有乱七八糟堆放在地上的广播喇叭器材。最后一间是公社广播室。广播员是一个长得很胖的女子,两条细长的辫子垂到了上衣的下摆。端正、丰满的脸庞表明她仍非常年轻。据说她已经结婚好几年,丈夫也是铁道兵。正因为同是铁道兵,许多人便把她当成一个远房亲戚,经常跟她开玩笑。如当着她的面,用冒名的四川腔学着她的广播:“现在的时间是六点三十分,现在的时间是六点三十分,工农兵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战斗(那时候兴把‘广播’称‘战斗’)。”她觉得不好意思,说:“那普通话该怎么说呀?你们教个标准的么。”
东边的那一排房子,我们营部也借了两间,作为卫生所,其它的房子还归公社所有。当时,这个公社才成立“革命委员会”,墙壁上还留有许多大标语和大字报。我不明白当时在公社办公的人怎么会那么少。他们的房子被我们占用了一半,也还是能照样工作,也没见得怎么拥挤。
公社的工作人员,我现在都记不清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认识的也不多。因为我不是办“外交”的,任何与他们打交道的事都用不着我参加。加上我这个人不善于交际,不喜欢与陌生人说话,就使这些人极其容易地从我的脑海里悄悄地溜掉。
我们这排房子的前方约七八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一米多高的土坯围墙,使大瓦房和围墙之间形成了一条窄小的天井。天井中段紧贴着围墙的地方,有两间低矮、简陋的厨房,一间是我们营部的,一间是公社的。与四川见缝插针种庄稼的特点相呼应,在这个小天井里也划出一块地种上辣椒和向日葵。此外,我们又在剩下的空间里栽上几根木柱子,拉上铁丝,晾上衣服。彻底地发挥了这个小天井每寸土地的潜能。
围墙的外面却是一个活跃的世界!它是一所中学,是一所寄宿学校,叫“重庆市实验中学”。中学的大操场就挨着我们的围墙。操场的另一侧是一道两米多高的砌筑整齐的挡土墙。挡土墙上边是一幢四层的教学大楼。这座由简单的几何线条构成的混凝土建筑物,孤零零地突出在一片灰色的平房和绿色的庄稼之上,很是显目,在很远的地方便能看到它。大楼正面的最高处,贴上特大的标语“亚夏解放军”(“亚夏”就是当时流行的新疆话“好”的意思),这标语贴得恰到好处,只要我们这些解放军一抬头,便映入眼帘。大楼的侧面,从上到下贴了八个大字:“革命无罪,造**有理”。
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根据上面的指示,学校要“停课闹革命”。即:虽然学生每天依然上学校,但再不上课。校长和老师都靠边站,学生自己管自己。
据说,当初这个学校也有两个互相对立的“红卫兵造**派”,只是其中有一派觉得力量太小,怕受打压,干脆不到学校来了。由是,由于失去了派性斗争的对立面。也就少了许多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或誓师大会了。我们看到的这些学生是安娴的、和平的。似乎女学生也比男学生多,这大概是由于不少男生们白天待不住,到外面找地方造**去了。剩下的男生一天到晚都在篮球场上打球。女生们则三五成群,在树荫底下看小说,织毛线,摆龙门阵(聊天)。我还发现她们特喜欢散着长头发,似乎这是由于她们才洗了头,想晾干那发亮的黑头发的缘由。其实,也有许多人即使头发晾干了,也不乐意扎成两条小辫子。扎两条小辫子本来是女“红卫兵”的标准发型,这可以从当时充斥街市的宣传画得以证实。对于这种现象,只能这样解释:她们是把这种披散的头发当作最新式的、“超社会”的发型。而她们这样打扮,似乎是为了表明她们不只是学生,不只是“革命小将”,而更主要的,已经是妙龄女郎了。
由于不必上课,教室对他们来说变成多余的东西。于是,我们便向他们借了这一教学楼的第一、二两层,住上一个连队——十八连——,而他们的男学生便集中住在三楼,女学生们则住在四楼。
看着这些不受纪律约束的年轻人,我的心里总是觉得非常亲切。这种友好的感情连我自己有时也觉得奇怪,难道是我还以为自己与他们一样都是中学生吗?不,不是的,我完全明白我现在已经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然而,恰恰是这些学生,他们勾起我对往昔生活的甜蜜的回忆。我觉得,我也曾经有过他们现在这样天真浪漫的时代,无忧无虑,自由散漫。
公社的那一排房子的前面,是一条公路。公路的另一侧,是一条盈满的小河。这条小河十几二十米宽。可能由于太小了,即使在详细的成渝地区地图上,也仅是用一条浅绿色的细线来表示,连个名称都没有。在这里,老百姓称它为“磨滩河”。
“磨滩河”十分美丽、秀气。碧绿的河水静悄悄地漫没着岸边像地毯似的绿草,好像是凑着耳朵轻声细语地诉说着什么心里话似的。河流两岸,挨着水边,排列着一簇簇茂盛的竹子。每一丛竹子有几十枝,枝枝相贴,拥成一团,色调柔和地点缀着这幽静的河流。这些竹子阻挡着人们的视野,使过路人只能看到两个竹丛中间的一小段盈满而悠悠的流水。如果你有机会站在某一跨越小河的小桥上观看河流的话,那么,两岸的竹丛又成两行美丽的屏障,像是保护着这泛着轻微波纹的河水悠悠向前。
小河在公社北边不远处突然拐了九十度的大湾,折向东边流去。拐弯后,河面随即展开,形成一个开阔的五六十米宽的大河湾。两侧的河床刚好又是缓缓的砂地,由浅入深,成为一个天然的游泳场。河流再往前不远,大约二百米,便是一个低矮的、简陋的石坝,河水翻过坝顶,飞下约二三十米深的悬崖,形成一个惊险的瀑布。
这是一幅非常动人的景色,当悠悠的河水开始从空中飞下的时候,还保存着它温柔的性格,它既不呼叫,也不翻腾,而是从容不迫地在笔直的悬岩上布下一张晶莹的、宽达二十多米的水帘,似乎有意在这里表示它的彩绸一样的连续性。悬崖半腰偶而溅起的水花就像缀在水帘上的图案。可是,悬崖太高了,流水不得不马上表现出它的飞泻的激情,好像它很快便控制不住了,咆哮着,疯狂地、不顾一切地扑向那神秘的深渊。在那里,它激起半天高的水花,这些乳白色的水花立即形成一片饱满的、白茫茫的浓雾,这些浓雾不停地翻滚者。它笼罩着深遂的河谷,严密地遮住了悬崖坡脚处的神秘面孔。人们只见瀑布从天而泻飞入茫茫的浓雾之中,被浓雾吞没了,融化了,只剩下透过浓雾逸出的低沉而雄浑的、使人觉得力量无穷的轰响。
浓雾的下方是一个天池似的湖泊。它在周围布满绿色林木的陡峭的山岭的衬托之下,更显出无比优美。清彻的湖水从浓雾底下流逸出来以后,便平滑如镜,纹波不起。恰与飞泻的瀑布形成了鲜明地对比。人们从瀑布走到这里。紧张的情绪会蓦然舒张,顿时觉得心旷神怡。
湖泊的出口处有一条细长而窄小的小石板桥,它低低地掠过水面。用角钢焊成的简陋的扶手栏杆,在水里映出轻轻晃动的倒影。
过了小桥,有一条修得很工整的石阶路把人们引进一个茂盛的树林子。林子里有好多整齐的红砖房子,缕缕炊烟轻轻地透过树叶升逸而去。这是水电站的家属宿舍,水电站就在瀑布边上的陡峭的山坡上。
这个村子也是很美丽的,这不仅是由于这宁静的环境,也不仅是几乎遮住了天空的树木,而更主要的,是它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有名的诗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上下工地都得经过这个地方。有一次,营长说:“这个地方能不能找到空房子?我说营部设在这里也不错,离工地也不算远。”
管理员说:“房子倒是有,可是行吗?连一条公路都没有,拉煤、拉米、拉材料怎么办?”
“说的也是,”营长说,“专门修一条公路到这里也太费工了。”
如果沿着公社面前的磨滩河逆水流方向向南走去,大约两三里路的地方,小河上便有一座修建得很美丽的铁索吊桥。吊桥的对面,是国家的一个机械部的第三设计院。这个设计院以一个小山岗为背景,依着山坡盖了许多现代化的大楼和设施。层层叠叠,互相掩映,很是气派。院里大树参天。美丽的林荫道、碧绿的葡萄园、整齐的石阶,硕大的广场,与周围的乡村景象形成极大的反差,仿佛是某个大城市的飞地。
我经常与这个设计院的知识分子相遇,因为他们晚饭后,总是三五成群、或男女相伴,沿着河边的公路散步。我也喜欢晚上遛达,以消磨掉白天中的这最后一个时刻。我很容易地依据衣着和举止把他们从来往的村民中分辨出来。我想,事情是很奇怪的,尽管我知道他们,可他们却不可能知道我,不可能知道这个穿着补丁军服、被太阳晒得黝黑的铁道兵也是一个“老九”。
那时候正值夏天,每天傍晚,这个设计院的许多年轻人沿着小河彼岸的小路来到公社底下的河湾游泳。大自然是慷慨的,给他们创造了这么好的场所:清澈的流水,松软的沙滩。路途又不远,好像是专为他们设立的游泳场。他们的到来,也使这里的气氛突然变得洋气起来。这些穿着颜色鲜艳的游泳服装的男女健儿,在水里欢跃、嬉戏。这时候,这里再也不是乡下的、偏僻的河湾,而是风景秀丽的水上乐园,是一个只缺冰淇淋小摊的水上俱乐部。



 河边草
河边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