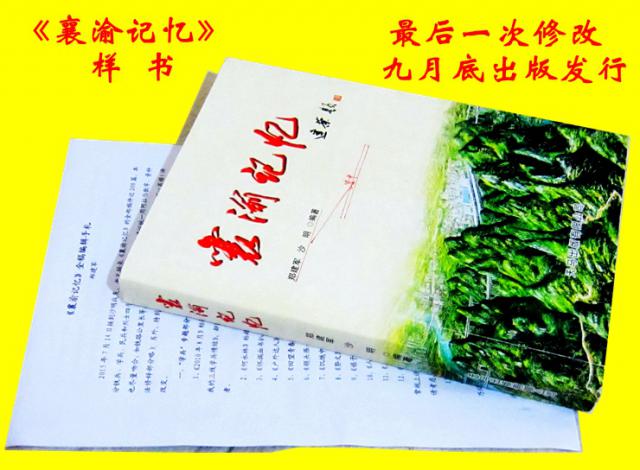从《襄渝记忆》看襄渝铁路
郑建军
在“三线建设要抓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下,如火如荼的三线建设波及13个省。其中有这样一条铁路,被誉为代号2107的秘密工程,如果不建起来,毛泽东主席“睡不好觉”,并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从1968年初开建,整整经过了五年,直至1973年10月完成,却给所有参建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视其为第二故乡,昼牵夜梦,不绝于心。
先让我们来看几组数字:
第一组:全长915.6公里的铁路横跨四省市20个县市;3跨汉江,9跨东河,7跨将军河,33次跨后河;穿越武当山、白云山、大巴山、华蓥山四大山脉;全线桥梁716座,总延长287.1公里,最高的大桥76米;有隧道405座,其中3公里以上的隧道12座,最长的隧道5330米;桥隧总长400多公里,占正线长度的46%,是当时中国现有铁路中桥隧密度最大的铁路;桥高隧长,有多线隧道13座,最长的1685米。
第二组:几乎同时上场人数近90万,平均每公里达1400人。其中,铁道兵集结了8个师、6个师属团、2个独立团,兵力达25万人,超过当时铁道兵总兵力的80%;鄂陕川三省组织民兵(工)上场60万;陕西省组织五地市六九和七〇两届初中学生上场近2.6万(其中女生5129人)。
第三组:整条铁路设立93个车站,其中有220处出了隧道就是桥梁,有36个车站建在桥上或桥隧衔接处。
第四组:牺牲和死亡超过2000人,平均每公里都会产生一名烈士。由于交通闭塞,需要修建公路便道2786公里,为铁路的3倍多。其中西段更为险峻,艰难至极,需架桥梁117座,修隧道177个,灌注上千条边坡地沟和涵洞,全段仅有9公里平面路基,1/3的里程,却占总工程量的2/3,全省4个不通公路的县,这里就占两个。由于“险隘连千里,秦塞路难行”,导致牺牲巨大,平均每公里牺牲和死亡达6人(含参建的民兵和学兵)。
一大串非凡的数字背后,是不能泯灭的记忆。看到这里,可能读者已经知道——不错,这就是襄渝铁路,这就是《襄渝记忆》。
襄渝铁路起点位于襄阳站(原襄樊市),由襄阳北站离开襄阳铁路枢纽经老河口东站,最后由北碚站介入重庆铁路枢纽,终点到达重庆西站。横贯鄂陕川渝四省市,东与汉丹、焦柳铁路衔接,中与阳安铁路相通,南与达成、达万、巴达、遂渝、成渝、川黔、渝怀铁路相连,是联络中国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对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
襄渝铁路由铁道部第二、三、四勘测设计院和电气化工程局设计,铁道兵担负施工。铁道兵集结了25万人形成主力,结合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电气化工程局和鄂陕川等省民兵(工)近60万,一字长龙排兵布阵,力量仍然不足,陕西省委又动员西安、宝鸡、咸阳、渭南和铜川等地六九和七〇两届近2.6万多名初中学生加入建设队伍。当时在900多公里的铁路建设工地上,旌旗猎猎,炮声隆隆,施工现场,波澜壮阔,其所投入的兵力不亚于当年的平津和淮海战役。经过五年时间,全线最后于1975年11月至1979年12月分别正式交付运营。
在这期间,参加施工的铁道兵、学兵和民兵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是他们让“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成为了历史。大巴山隧道处于川陕交界处,全长5332米,是襄渝铁路上最长的隧道,该隧道集瓦斯、岩溶、断层、涌突水、高地应力、大变形等不良地质病害于一体,堪称“地质博物馆”。日本专家考察时,曾给大巴山隧道判了“死刑”,说这里是铁路的“禁区”,要么报废,要么改线或重建。桥梁和隧道的总长度占铁路总长度的46%,据参加成昆铁路建设的铁道老兵说:襄渝铁路的修建难度超过了成昆铁路。在全线20个滑动工点,共灌注了288根锚固桩,长度相当于往地球深处插进750公里长的巨型锚钉,被《解放军报》头版头条予以报道。
襄渝铁路可以说是当时我国铁路建设史上最复杂、最艰巨、最困难的一条铁路,由于山高谷深,线路桥隧相连,有220处出了隧道就是桥;有36个车站一头建在桥上,一头建在隧道里。线路所经地方,人烟稀少,交通闭塞,需要修建公路便道2786公里,为铁路的三倍多。铁路沿线地质不良,岩层破碎,断层多,有的地段山体移动,有的还有放射性物质,滑坡、崩坍、泥石流、地下水不断出现。特别是在陕西境内,264公里的铁路线,桥隧总长206公里,有186座隧道,250座桥梁。桥隧折合单线长达215公里,为陕西段线路长度的81.5%。就是说襄渝铁路陕西段基本是在大山“腹中”穿行,是一条名符其实的“地下通道”和“空中走廊”。
囿于时空差距,我无法将襄渝铁路与万里长城作比较。犹如叶剑英元帅给铁道兵的题词:“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襄渝线上,参建者就是凭着对领袖的敬仰,靠自己的一双铁手、一副钢肩,令高山低了头,令江河让了路。
40多年过去了,三线、襄渝建设的不朽,成为当年参建者一场不醒的梦。
坐在飞驰的列车里,桥梁上“咣当咣当”的轮轨撞击声让人感觉刺耳,隧道里“呜呜嗡嗡”的噪音让人觉得郁闷。朋友,谁曾想到在这大山里是谁建造的这条钢铁巨龙?他们又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抛家舍业与孤独做伴,风华当年却华发早生。生死来临之时,甚至把在棺材里能多放两个馒头作为希望;面对牺牲,其父母毅然又将牺牲者的弟妹送到部队;大成隧道洪水倒灌,一次牺牲32人,救援勇士的遗书中却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能把家里的帐还上……(写到这里,噙在眼眶的泪水再也忍不住,顺着腮边滚落下来)
“文章无求召凤仪,雪泥信能印鸿踪。”用西安学兵张有安的话如是说。但当年的参建者并无遗憾。他们著书立说、握笔描绘、网站撰文、影视讲述……不过是“我为青史添一星”。曾经10次重返襄渝故地、5次出书、多次义捐当地小学的沙明做了很好的概括:“他们追求的信念是宽容并不忘记,沉默并不冷漠,有怨并不有悔,回望并不蹉跎。”
越是磨难越能锤炼人的意志,越是坎坷越能陶造人的风姿。有人说:“我感念三线生活对我的启迪,那是对意志、能力等立世素质的一种储备,是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段历练,正是有那碗垫底的老酒,让我后来跨过了所遇到的很多沟沟坎坎。”40多年过去了,参建者可以忘掉很多,但如火如荼的三线岁月和襄渝铁路记忆,则是伴随其一生的不朽。不信的话,读者有机会可以去问一问任何一个健在的参建者以作验证。
他们或三五成群,或成群结伙,甚至上百人有组织的重回故地,去祭奠曾经的战友,去寻访曾经的驻地,去回望曾经的桥隧、路堤和深山沟壑……杨米贵用手中的画笔十年成就128米的“襄渝铁路”油画长卷,陈瑛丽举家回迁紫阳创立闽秦茶业公司,李国强一次性捐出10万元给当地政府重修烈士墓……朋友,当你通过本文开头的几组数字了解了这些,你还会为轮轨的撞击噪音而感到刺耳和郁闷么?
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每一次重读,都是一次意志的历练。再次擦干脸颊上的泪水,闭目静思,驻笔小歇,不再赘述《襄渝记忆》中所记录的豹之一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襄渝记忆》中去领略襄渝建设的不朽和不老的“青春回望”。最后还是说点轻松的吧。
在襄渝铁路线上有一道奇观,那就是各式各样的铁路桥。这些桥有大有小,还有造型独特的钢梁桥。这些多姿的铁路桥是连接铁路运输大动脉的锁链,更是贯通鄂陕川渝四省市的“彩虹”。襄渝铁路沿线多是重叠连绵的山峰,群山之间,碧绿清幽的江水急急东流,一座座的铁路桥横架在急流险滩之上,一座座桥下江水湍急,桥影如月映在水中。行走在高高险险的两座大山之间,眼前便会出现一座气势宏伟的桥——紫阳汉江大桥,这座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铁路钢梁桥横跨在汉江之上,虽然只有437米长,但桥高70.5米,大桥两边还设有宽宽的人行通道,就像一道彩虹连起了汉江两岸。
长时间驻足在紫阳汉江大桥上,山清水秀的紫阳城尽收眼底。静坐在铁道边,让思绪乘上列车继续向大巴山深处行进,领略着“险隘连千里,秦塞路难行”的奇观。山势更加巍峨,铁路就像一条绸带从群山险峰中穿越,悬崖峭壁处处林立,险峻峥嵘随处可见,有些车站不得不建在桥上。桥是襄渝线上的风景,更是大动脉的脊梁,也是襄渝铁路的支柱。襄渝线上的一座座铁路桥屹立在山间,跨越着河流。正是它们把江河的北岸和南岸、东岸和西岸连在了一起,使线路两侧不相干的大山牵起了手,这些多姿的铁路桥为铁路运输事业奉献着光和热,也在襄渝线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