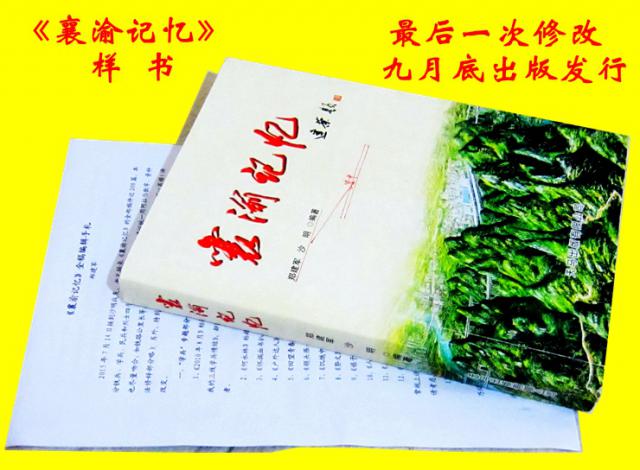趣谈铁道兵老战友贺应明创造的高超纪录
我们1962年重庆入伍的铁十师老战友,从1992年的参军30周年纪念聚会至今,大小聚会已经举行了多次。最初,战友们把纪念性的聚会定为3年一小聚、5年一大聚。实际上,人数较少、情话性的聚会经常都有举行。或者过年过节了,或者有战友过生日了,或者有战友从外地来渝了,大家都要聚一聚。聚在一起忆当年,回顾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战友之间的深情厚谊,总是越说越有味,越说越觉得聚会应该更勤一些,联系通知参加的战友更多一些。于是,从2011年开始,大家约定:参军纪念的聚会,每年举办一次。
2015年的聚会,是参军53周年纪念会;战友们年龄最小的都已经进入古稀。聚会中,战友们回顾在部队的日子,那可是说的有滋有味,不时还有一些互相打趣助兴。我发言的时候,回忆了几位老战友的趣事;其中特别提到贺应明战友的一些事迹。贺应明战友在当铁道兵期间,创造了两项虽然不见经传,却也堪称冠军的“纪录”,那还是很令战友们赞叹、佩服的。别小看这几项并不起眼、也不轰动的“纪录”,我相信即使是在全铁道兵家园中间,恐怕也是少有、罕见,甚至是唯一的。所以我把它整理成一篇回忆录,贴上铁道兵家园的网站,让大家都见识见识,看看原滋原味、最接地气的铁道兵精神是什么样子。
(一)当上铁道兵,他一个月长了40斤。
贺应明战友报名参军体检时,身高是1米655,体重是88斤,明显是个瘦子。说起来笔者更瘦,身高1米64、体重84斤。为什么?三年大饥荒,国家经济困难,老百姓吃不饱啊!笔者在以前发过的回忆录曾经写过,我们这一批战友是在战争一触即发、国家紧急招兵,热血青年纷纷应征的形势下勇敢入伍的。因此,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全部是“城市兵”;第二,相当一部分人是投笔从戎,有比较高的文化素质。贺应明战友就是其中佼佼者之一。第三,还有一个特点,大多数人都是瘦子。针对这个问题,国家把征兵体检标准下调3公斤,把陆军体重45公斤合格下调为42公斤合格。笔者体检时,医院护士把磅秤标尺移动到42公斤刻度,那个秤砣似起非起,也算是勉强合格。
贺应明战友报名参军时是西师附中(即现在的西南大学附中,地处重庆北碚,有名的重点中学)的应届毕业生。虽说是投笔从戎、而且人长的很瘦,但是在他身上却没有常人想象的那种文弱“秀才”的影子。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从小在嘉陵江边长大。劳苦人家的孩子从懂事开始,就要干体力活;挑担、拉车对于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常常在寒暑假或者课余时间去干力气活,挣点学费。重庆建设工地上常见的抬连二石(铁道兵所说的条石)那样的重活,他也能胜任。所以在中学里,他被选成了班里勤工俭学的劳动委员。
既然都是瘦子,穿上军装的第一个强项,就是能吃;因为参军前大家的粮食供应定量都很低。贺应明是应届毕业生,定量是每月30斤。笔者就更惨了,小学教师,18斤定量加3斤工种粮,满打满算仅仅21斤,还不够半个月吃(那时,煤矿井下采煤工人定量最高,是54斤。像我们班的杨显林战友,采煤工,身体就很壮实)。当兵的定量是多少?40斤。不过从征兵地到老部队驻地,路上行程这一段时间是不讲定量的。军列每到一处军供站,食堂里吃饭基本上是管饱、尽胀。所以呀,军列奔驰之中,不时地就有人向接兵干部喊:“我要屙㞎㞎!”军列车厢大多是60吨货车车皮,中间开门,两头都隔成上下两层、铺上苇席;新兵战友上去放开背包就成了通铺铺位。为了安全,车厢门拦有一个爬往上层时用的梯子。躺在上层铺位的人要屙㞎㞎,从梯子下来,由两个新战友拉着双手,屁股撅到车厢外拉大便,重庆话叫“屙吊岩屎”。吃得多就拉得多,一天拉两次的是大有人在哟!(嘻嘻,笔者的肚子小,肠胃功能也差,只拉一次,不好意思。)到了老部队不久就体检复查,笔者一过磅秤,93斤!但是,医生说我心脏有杂音,差一点把我退回地方去(他问我早操跑步累不累?我坚定地说不累。要是说累的话,可能就得打道回府了)。半个月长了9斤,也没有把我退地方;我心里暗自为自己庆幸。当时,并没有十分留意别人长了几斤。贺应明和我不一个班,他长了多少,我可是一直不知道的。
10年以后的1972年冬天,我随接兵小分队到山东梁山去接兵;在新兵团训新兵期间到连队了解收集训练情况。我们49团三营新兵连的连长、指导员汇报说,有一个农村兵新战士创了纪录,一个月长了28斤。他们说玩笑话,感慨这位新兵比猪还长的快!又过了40年,重庆老战友聚会时我讲这段趣闻,贺应明战友马上回答我说:“那不算多,我一个月长了40斤!从88斤长到128斤!高文星更多,是42斤!”呵呵,我差一点惊呼起来!咱们铁道兵重庆战友创造的这一纪录,恐怕真的应该算是全军第一也!
(二)装卸卡车,他一手抱一袋水泥。
能吃不是本事,能干才是英雄本色。刚参军我们能吃、长的快,根本就是补亏。因为参军前瘦,那是3年全民大饥荒饿的。我们这批重庆城市兵,吃饱之后立马显现出令人竖大拇指的吃苦耐劳、善打敢拼的勇武精神。
虽然我们是临战前的应急入伍,但是军列没有把我们拉上前线,而是意想不到的被拉到了首都北京。虽然我们是铁道兵,但是我们也没有立马去修铁路,而是参与了国防建设的保密工程。现在说,两弹一星,那时候只知道可能和火箭有关系。我们铁十师,从抗美援朝回国之后到了大西北,修的铁路要保密。干什么用?后来放了原子弹才知道和它有关系。我们49团从西北到北京,团部驻五棵松。全团三个营:一营驻南苑东高地,二营驻云冈。我们三营营部和九连先驻团部,后移防到永定路,离铁道兵兵部仅几百米。所以,九连是当时离铁道兵兵部最近的连队。
我们担负的大多是一些杂项任务和零星小工程。而总的工程单位是总参五院,总院下边的一分院在南苑、二分院在永定路、三分院在云冈。任何人进出分院大门,都必须凭出入证;进出分院里面的一些楼,即便是加挖电梯基坑,还要办临时的出入标签夹在出入证里。分配给我们铁道兵施工连队的这些杂项任务中,也包括有装卸、搬运一类的工作;比如,从在五路的军用火车站搬运钢材、水泥到分院。因为我们是部队、是军人,即便是这样平凡的任务,干起活来也跟打仗冲锋似的。笔者记得,强运水泥,一辆解放牌汽车装80袋(4吨);班长掐着表,我们装一车仅用8分钟。大家喘着粗气,重庆话叫“气齁八齁的”。我身体很弱,每次只能费力地抱起一袋;而我们班的杨显林两手提起一袋就往汽车上扔。
贺应明就更不简单了。别看他个子不高,他可是每次搬两袋,一手一袋哟!肉不白长,饭不白吃,很为我们重庆兵争面子。
在我们49团之前,承担五院这些工程的是工程兵的一个团。根据二分院的反映,我们49团的素质和战斗力大大超过他们。因此,五院曾经提出,将我们团从铁道兵调出,并归他们的编制。这个提议反映到罗瑞卿总参谋长那里,铁道兵领导不同意,说铁道兵同样需要高素质的部队。据说,是铁道兵副政委王集成前去罗瑞卿总参谋长那里据理力争的。他俩是曾在一起的战友,关系很好;一个个子高,外号“罗长子”;一个个子矮,外号“王矬子”。争的结果,我们49团仍留铁道兵。这时也恰好,毛主席发了“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铁道兵要把十师包括49团调往成昆线。于是,我们49团千里大转移,于1964年9月到了四川峨眉。
(三)360斤的钢拱圈,他扛起来走了50米。
贺应明能干,进步就快。参军两年多,他光荣的入了党,还从列兵到排长,连升了五级。升得快也算一项纪录吧;咱们这批重庆兵,升得这么快的当然不止老贺一人。但是要知道,那时候升得快全凭实实在在的干!部队有一句打趣的话,叫做“挣表现”。当铁道兵,如果怕苦怕累,偷奸耍滑,那就不可能升的快。表现不好泡病号的,部队也有打趣的话,叫做“压铺板”、“晒地瓜干”;这样的人当然就不想入党提干。反正不管怎么说,咱们当兵那会儿,是全军全国学习雷锋的年代,可没有听说过入党提干像如今搞“市场经济”、军队经商这些年,竟然要花钱,成了买卖!
要说表现,咱们重庆的这批战友的表现那真是可圈可点;五好战士,技术能手比比皆是。到了成昆线,我们这一批战友全是经过全军(1964年)大比武的真资格的老兵,不论升的快的还是升的慢的,都是工作中的骨干、技术上的师傅、对新战友传帮带的典范。
为了修成昆线,铁道兵扩兵10万。1964年冬季征兵补充到部队的1965年新兵,应该说是修成昆铁路出力最多的一批兵。从那一年起,服役期从原来的3年改为5年。补充到49团的这一批战友,基本上都是农村兵,城市兵很少。主要来自温江地区和成都附近区县,像郫县、金堂、什邡、广汉,新都以及成都金牛区等等。这批来自农村的战友也很能吃苦耐劳,不惧重干体力活,以能挑善抬而引以为豪。他们听说贺应明排长是来自重庆大城市的城市兵,免不了心里想就,他人也不高马也不大,看不出有多大能耐。于是就找机会要比试比试,来个挑战赛。赛什么?最简单的就是掰腕子,贺应明是掰遍全连无敌手。单手比不成就比双手,来个双手扭扁担;结果,一条最结实的扁担被扭成了两半。在百家岭隧道工地上,战士们提出要和贺排长比谁最能挑重担。灌混凝土用的石子儿,有战士一肩挑起了两挑(4筐),问贺排长敢不敢?贺应明二话没说,叫大家摞起四挑(8筐),用大抬杠挑了起来,引来战士们一阵欢呼和惊叹!大家一时兴起,要比一比谁能把隧道打拱用的钢拱圈扛起来。一根钢拱圈大约4米长吧,重有360斤啊!经过比试,全排战士没一个扛得起来。贺排长把手一挥,叫战士抬起来放到自己肩膀上;他不仅扛了起来,而且还走了50米!
这样的比赛纪录,不知道咱们铁道兵别的部队有没有、有多少?这样的排长,这样的铁道兵干部,战士们能不服吗?作为参加过修建成昆线的老铁道兵,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成昆线就是用这种精神修起来的呀!
(四)高层首长挑选警卫参谋,他去西工指转了一圈。
扛钢拱圈之后不久,贺应明被提升为49团二十五连(就是我们刚参军时的老九连,1965年扩编改为二十五连)副指导员。原来的副指导员刘明章任指导员。刘指导员是1949年参军的老首长;贺应明刚参军进九连时他就是副指导员。刘指导员是个热心爱才的领导,眼看贺应明从战士成长提拔为自己的副手,他从心里高兴!老带新,老新联手,连队搞的红红火火,各项任务完成的很出色。
1966年的春夏之交,地处峨眉三峨山下的百家岭隧道快要贯通了。连里忽然接到电话通知,叫贺应明立即赶到西昌,去铁道兵西南工地指挥部报到。组织部门的指示说的很清楚,领导机关看上贺应明了,要调他去给首长当警卫参谋。跟哪位首长?李井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三线”建设总指挥。当中央一级首长的警卫员,先试用,再提拔。刘指导员好舍不得呀!但还是向贺应明表示祝贺。好干部谁都想要,连里是留不住的!
告别了营、连首长,告别了连队和战友,贺应明按时来到了月城西昌的邛海边上。
然而令他意外的是,保卫部领导没有带他去见首长。在问完他探过亲没有之后,安排他先回重庆探亲,警卫任务等探亲回来再说。咱们这批重庆兵参军时国家规定服役期是三年,临近满期却一下子改为五年。贺应明服役将满四年,西工指安排他提前探亲,也是一个意外的喜悦。
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探亲回到西工指,警卫任务仍然不能落实;指挥部的首长们已经基本上见不着。因为红卫兵开始大串连,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西昌,贺应明能见到留在工地指挥部机关的首长还有一个,就是副政委刘建章。刘副政委这时候每天用餐,也得自己到食堂站队打饭了。贺应明陪同刘副政委到邛海游过一次泳。他俩边泳边聊,游到邛海深处;刘副政委还夸嘉陵江边长大的贺应明水性好。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哪位首长了。
“走资派”首长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贺应明可是闲得无聊的时候。那时候,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可以有“造**派”,可以搞“四大”;师以下部队则不搞。贺应明在指挥部机关谁也不认识,更没有兴趣参与那里的“运动”。闲的无所事事,天天加深着他对老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思念。西工指保卫部的李部长知道他的心思就对他说:看来这运动一会半会不会结束,首长也回不来了,你又没有正式调入机关,干脆还是回去吧。于是,贺应明在工地指挥部耽误了好几个月转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了49团。
(五)后记
战友们曾经打趣贺应明,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咱们这批战友里面他可能升的更高、升的最快。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参谋嘛,不说高灯之下,就说干部级别,至少也是正团。
不过老贺可是把这一段看的很淡很淡。
回到49团,他曾经担任过女子民兵连的连长,后调任群工股干事。转业回地方后,曾任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中央在渝单位)工会常务副主席。咱们重庆战友参军30周年聚会,请他们单位提供过场地,他是战友会的发起人和筹委会成员之一。
今年是战友们参军54周年;照例要举行聚会。贺应明战友仍然是筹备组成员。现今七十有五的贺应明战友,已经扛不动360斤的钢拱圈了。他说:“社会上不是每个人都有战友,更莫说我们当铁道兵那么艰苦。艰苦战斗生活中结下的战友深情,永远值得纪念。每一次聚会我都参加,每一次聚会都会加深战友们的感情。”
(备注附记)
1,一个月长40斤体重,得吃多少饭?当时士兵粮食定量一个月40斤,够吗?
一方面,连队有一些库存,对新兵会多照顾一些。另一方面,还要搞一些副业,例如每个连队都在营区附近开有菜地,建有猪圈养猪。新战友也有饭量小,吃不完定量的。贺应明所在的四班,有原来在地方就粮食定量高的战友。比如刘国良,参军前是煤矿井下工人,定量54斤;在重庆吃的大米饭,到部队在北京吃窝窝头不习惯,咽不下,就让给战友吃。有战友能一顿吃10几个窝窝头甚至更多的。所以长的快、长的多就不奇怪了。
2,笔者1968年在《铁道兵》报社学习时,和当时负责日常出报的张希尧副社长(曾任李寿轩司令员的秘书)聊天,听他说过报纸宣传被找毛病的事。
文革初期,造**派对军队报纸也有吹毛求疵、挑毛病上纲上线的。例如,把一张报纸透过阳光找毛病。那时报纸第一版常常是大幅毛主席像。第二版常常有大批判文章,有什么“走资派”、“叛徒”……之类的字样。发现这种的字样透到了毛主席像脸部,于是就声称该报纸对毛主席不恭,“用意恶毒”等等。另外那时是铅字排版,铅字架上的铅字按字典的偏旁部首排列。捡字工人不小心检错了字,校对又没有发现,也会惹来麻烦。例如《铁道兵》报社的铅字架上,为了捡字快一点,把毛主席语录“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前两个词组铅字是放到一起的。工人捡下来放进字版合放反了;印出来成了“全完”“底彻”为人民服务,于是被抓辫子声讨。还有把“革命闯将”捡成“革命闹将”、甚至把毛主席和革命群众的“血肉联系”捡成“血债联系”的,更是成了罪过。《空军报》出现这些问题,汇报给了林彪。“林副主席”特做批示,不要把技术问题上纲上线,这才过关。
除了这种形式主义的揪错,也有找宣传方向等方面问题的。例如《铁道兵》报抗美援朝在朝鲜时,表扬两位抢修铁路的英雄人物。扛枕木,一个是“老黄牛”,能扛3根;一个是“牛犊子”,敢扛2根。《铁道兵》报(当时叫《铁军报》)一报道,这两位英雄就不敢每次扛1根了。结果很不幸,两位英雄都累死在了战场上。有造**派认为这是《铁道兵》报的历史罪过。
笔者的本回忆录讲贺应明战友扛钢拱圈的等纪录可是真的事实。如果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们这位老战友不会被笔者的新闻报道压垮、压牺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