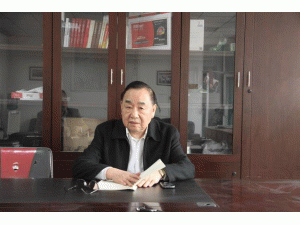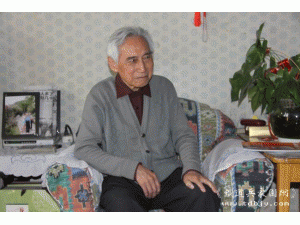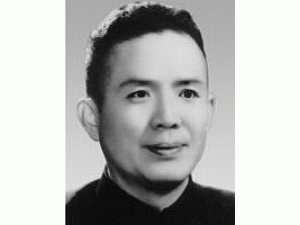采访人物三张敬心:两次出国参战的经历让人难忘
张敬心,男,1928年11月出生,河南濮阳人。历任铁道工程第6师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离休时任6师政治部副主任(正团职)。
第一次出国:抗美援朝
我是1953年1月份入朝的。那时的空中全是美国人的天下,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是“地上没有高炮防卫,天上没有飞机掩护”。美军对铁路枢纽新安州、西浦、价川“三角地区”,实施重点轰炸。尽管敌人炸的很厉害,但我们还是用老办法:木笼填石基础,立木排架作桥墩,用工字樑代替其钢板樑。
战争年代很残酷,但大家始终斗志高昂 ,正如连队文艺组唱的快板一样:
铁道兵可真棒,抢修现场有戏唱。天上飞机飞,地下炸+响,压轴好戏全登场。
美国飞机怪模样,撅起屁股把屁放,咚咚咚,乓乓乓,懵头懵脑乱放枪。
铁道兵战士多英爽,光看戏不鼓掌。又吃饭又喝汤,吃饱喝足山边躺,避风又朝阳,呼噜呼噜进梦乡,养足精神铆足劲,敌机滚蛋俺再上战场。
同时大家有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工地上紧张有序,喊着号子干得热火朝天:同志们呀,加油干,挺直腰杆脚步稳,迈开大步过沟坎,一步又一步,一步一层天。今天俺们吃点苦,为国为民保平安。
看看吧,抗美援朝战场上“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就是这样拼命干出来的。
最难忘的是当时师里有一个护士叫陈素云,泼辣能干。当时医院设备、医疗条件简陋,为了抢救危重伤病员,特别是有些战士负伤后腿部化脓,她就用嘴吸,后来成为全师立功的典型。
第二次出国:抗美援越
1967年,六师挑选了四十余人去越南学习,我被挑去了,待了三个月学习作战技术,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当时咱们一师有个排在那施工,二师有个一支队、步兵、高炮队都在那。那里气温高,大家住在山洞里,虽然穿的是背心短裤但热得都不行,坐车下来会起一身痱子。那里容易得肠胃病,所以喝稀饭都要吃大蒜。在那晒脱了一层皮。经常还要躲飞机。战士经常失踪,后来部队规定外出不能一人,必须两个人。越南蛇特别多,走路都得拿着根小棍,防止蛇咬。什么都不拿可以,小棍不能不拿。
经历过抗美援朝战场的洗礼,战争把人们变得聪明了,在越南就有经验多了,很好地减少了伤亡。比如说在方便生话,方便施工的前提下,驻地、车辆、器材适当分散,插上树枝,披上草网,当时的口号有〝驻地上面不露房盖,路上行人不见墙壁,做饭不冒烟,点灯不见亮,晒物不见物〞。在驻地、工地,依椐地形地貌,构筑防空工事.防空工事有两个进出口,而且必须设拐弯,人员防空要求做到〝防空必进洞,进洞必拐弯〞,进了防空洞,一般还是安全的.工事防护强度很大,即使敌人火箭命中,工事内人员、器材也不会受损。
两次出国叫人很难忘记,国内修路也顺带说说吧。国内虽然没有了战争的残酷,可自然条件、施工环境也是很可怕的。
1964年,修建嫩林铁路,进入大兴安岭。当时那个地方的林业工人三进三出,都没有在那待下来。气温能达到零下50多度,狼多,环境恶劣。后来我们的铁道兵部队3、6、9师进去,师部住在“雷击区”,自己盖上房子,待下来了,那个地方没有名字,后来战士们自己起名叫“三荣岗”。部队到了那里搭帐篷,用地火龙解决取暖问题。晚上战士不能出去帐篷,拴紧帐篷,白天部队出去修路,家里各留守一个人劈柴火,烧地火龙,确保温度。后来林业工人才进去慢慢多起来,后来发展了一个林场。
1968年,修建襄渝线,穿大巴山,当时沿线地质复杂,许多地段上旁悬崖,下临深涧沿线山高峰险,川大流急,路窄险、两人不能同时并着过,一不小心会跌下去。山里多年没有老百姓进去,老百姓几十年也没下过山。老百姓称为“光棍岭”、“一线天”、半坡崖,比较危险。没有进山的路,部队进去先开挖便道,工程和生活物资主要靠肩挑背扛,自己建房、自己选点。我们当时住在毛巴。我们称“头顶一线天,脚踩三块砖”,当时修建四线隧道、四线桥、马溜车站。车站是把山头平后上盖的房子。带着四川的民兵团施工,一个团管几个民工团施工,民工团的团长都是武装部长、团县政委、宣传部长等担任。在任务重、工期短、兵员不足的条件下,部队坚持按时完成了任务。当地流传着老百姓的俗语“毛毛雨是好天,下着雨照常上班。”施工中桥大、隧道多。当时,二营一个广西的战士,在打吴家湾隧道时,发生塌方,他进去救了几个人,最终自己也牺牲了。
75年襄渝线收工后。我来到新疆修南疆线。当时30团打隧道时有一个二营营长叫周森林,山东人,是个能啃硬骨头的人。他胆子大、懂工程、肯钻研、能吃苦,每天盯在施工一线,同战士们一起干,吃住在现场,从来不去参加会议。别人不敢干的,干不下来时,他都能干下来,后来提升为副团长。后来26团在打三线隧道,打不下来。李师长就把他从二营调去,带着两个连过去,打攻坚战把隧道顺利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