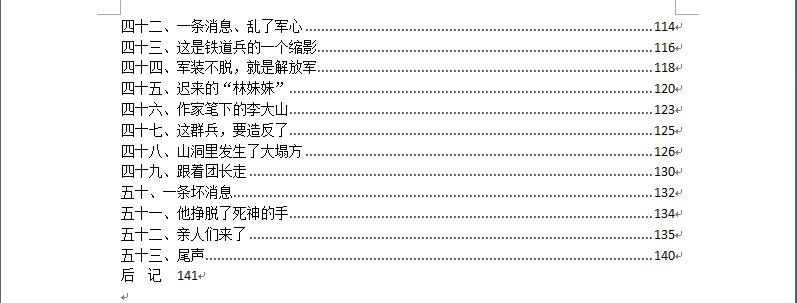九、这样的军营?不敢相信
汽车车队驶出操场,驶出营区,首尾衔接,沿一条土路,在山里上坡下坡,蜿蜒如蛇,上山坡时如人行走,哼足了劲,下坡时,车如飞,听不见机械声,经左转右绕,驶进了一条山谷,又从这条山谷里出来,眼前一亮:
啊!草原,众人嚷起来。同车的有云南、广西兵,云南的说话还有点汉语味,广西兵嘴里叽里呱啦的就像外国人,他们的手指指点点的发着感概。晶晶说:“这草原真美,真跟画中一样。”是啊!蓝天、白云,碧绿的草原,像厚厚的地毯。汽车在这碧绿的海洋里穿行,它一边连着很远的低而缓的绿山坡,另一边则是汽车绕行的山脚,前面随汽车的走向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偶尔可以看见一片游动的羊群,就像那云彩落在了草地上,羊群的一边是一个骑马的姑娘,她头上裹着彩巾,手里像是拿了鞭子,也在随着那地上的云流动,别看那姑娘在画中的位置不大,但却是画中的主角,因为大家都想一睹那姑娘的芳容,可汽车只是一边绕着山、一边沿着草原的边沿奔跑,并不近前。
啊!真美,真美,晶晶诗兴很浓,却是没有下文,爱军接着说:“美是美,只是这草并不太深,没有了诗中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
汽车拼命的跑着,草原上原本没有路,铁道兵来到这里,汽车才轧出了路,遇有弯道,后面的汽车冲上来,前面落后的不服气,又赶超过去,这样来回的赶超,把车上的战士们悠的是前仰后合,铁道兵的司机们真野。
前面出现了一群牛,他们惊得全忘了吃草,昂着头,好奇的看着这些过来的军车,并不逃窜,爱军说:“这么多的牛,没有缰绳,由着性子的乱走,像野牛,这将来怎么用啊?”“是啊,这得训练啊”和爱军一个新兵连、熟悉爱军的老乡在车上附和。
再往前走,山脚下出现了新修的铁路路基,隔不远,路基上就有一小伙穿绿衣服的人在干活。车随着山脚来回的绕,绕不动了,山坡上就出现了一个山洞口,那就是新修的铁路隧道,隧道口也有穿绿衣服的年轻人在工作。车绕过去,山那边就又出现一个隧道口,又一伙穿绿衣服的年轻人在干活。就有人问:“班长,那是我们老部队的人了?”“是啊!”那叫班长的答应着。这也是一个训练新兵的班长,但不是小个子班长,小个子班长此时不知坐的哪个车,听他说他是十八连的老兵。又有人问:“班长,在这里上班就不带领章、帽徽了吗?”“不用戴,每天干活脏兮兮的,戴了还影响军容,再说了,这里没有一个老百姓,就我们这些兵,戴不戴没意思。”“啊”车上的新兵们大惊小怪。
车继续在山脚下、草原的边沿上奔跑,忽然,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土房子的院落,朝着路口、土房子的边上,一些着军装的军人,手里拿着锣鼓在迎接新兵,两辆军车开过去,那些军人立刻就敲了起来。
爱军的车越过了这些土房子,“还没到啊!”晶晶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大家说。就这样,车又开了很长时间,越过了两三座这样的土院子,前面又一个土院子出现了,两台汽车就驶离了大路,朝土院子冲去。
再说,这土院子冲路口的地方,站满了手拿锣鼓的军人,见汽车过来,一个穿四个口袋的中年军官喊:“开始”这群手拿锣鼓的军人就“咚咚呛、咚咚呛”地敲了起来,汽车到了土房子跟前戛然而止,老兵们围上来,驾驶室门开开,下来了指导员、陈排长,那中年军官和指导员互致敬礼、握手:
“哎呀,指导员,可把你盼回来了。”
“哎呀、我也想你呀连长,近来工作可好?”
“忙坏了、忙坏了,你回来就好了。”二人站到一边说了起来。
车的后箱门打开啦,老兵们接上面新兵递下来的背包、脸盆,新兵们一个个地下了车,新老兵们交织在一起:老家是哪里?新兵连辛苦了。我家是云南的。。。。。。我家是广西的。。。。。。我家是河南的。老兵同志辛苦了。不客气,到了老部队,就算到家了。。。。。。。新老兵正在热乎,人群里突然钻进来一只大黄狗,瞅着这个新兵的脚嗅嗅,瞅着那个新兵的脚闻闻,新兵们吓得只往后退,连长吼道:“阿黄,闻什么闻?没看见三点红?都是战友,一边去。”连长指了指旁边,那叫阿黄的狗就乖乖地蹲在了一边,眼巴巴地看着这群新老战友们亲热。
爱军下了车一瞅,整个的境况便一览无余,好几座顶是油毡、墙是土坯的房子,围成了一个大院子,房子与房子之间有很大的缺口,到处都通向草原,没有围墙、没有大门和卫兵,土坯房子的墙壁上是红土写的大字: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艰苦为荣,劳动为荣,当铁道兵为荣。爱军心里嘀咕:竟有这样的军营?怎么连个打仗的字眼也没有?
爱军心里正惶惑,哨声响了,连队集合,新兵们在院子的正中间,坐在自己的背包上,老兵们站在新兵们周围,连长作了一个很短的讲话:“新战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先锋连,你们新兵连辛苦了。”老兵们鼓起了掌。连长环视一下新兵们说:“我姓牛,叫牛连长,啊、不,也可以说是你们的老兄。”爱军心里好笑,新兵连的连长姓崔,老部队的连长姓牛,这二人要是在一个连队工作,那不就叫‘吹牛’了吧?
牛连长继续说,但他的声音没有崔连长的细:“今天,就算到老家了,从今天起,我们也就成弟兄了,我们就在一起干活、劳动了,就在一个锅里耍勺头了,一个锅里耍勺头、锅铲还能不磕磕碰碰?啊,要在一起好几年,免不了,大家要担待”他转向指导员:“你说吧,大家爱听你的。”
一脸妈妈像的指导员上来了:“同志们哪,我们送走了一批大哥哥,又迎来了一批小弟弟,没有走的老兵,又成了大哥哥,我们的老兵啊,要有个大哥哥的样子,要看管好这些小弟弟,同你们一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很多同志得有个适应过程,啊,在工作分配上,要掂量掂量,要是把哪个新兵累着了,要闹着回家,我拿你班长试问。各位班长,听到了吗?”“听到了”班长们回答。
接着指导员念起了分到各班的新兵名单:“张大山,马力大,尚北京。。。。。。”这些新兵站起来,老兵们簇拥着这些新兵,各向各的班走去。指导员又念:“爱军,吴胜利,”听到念自己的名字,爱军站起来,马上就有一高一低两个老兵过来,高的接过背包,低的接过脸盆,还有几个老兵簇拥着,向一排的土房子里走去。
一进屋,那高个子就把爱军的背包打开,说:“这是我的铺,就挨着我睡吧。”不多会,其他几个新兵也安顿好了,老兵们挨个给新兵们每人倒了一杯热腾腾的开水,递到手中,一个黑黑的、敦实而又有点腼腆的老兵说:“我是班长,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大家介绍介绍吧。”那高个子的战士说:“我姓高,也就比你们多一年的兵,以后,新同志有啥困难,尽管说,我一定努力帮助。”那宽额头、尖下巴的小个子兵开口了;“我姓孙,叫孙---”班长接了口:“孙悟空”众人都笑了。那小个子的兵着实有力,冷不丁站起,抱住班长一下子把他撩倒在了铺上。“哈哈、哈哈----”老兵们笑的更响了,新兵们不敢,班长红了脸:“胡闹,正开会呢,接着说。”
这把班长掀翻的小个子兵叫孙玉生。
老兵介绍完后,新兵也各自作了介绍,爱军谦虚地说:“刚到老部队,什么也不懂,希望老兵们多指点,多包容,把班里的工作搞好”班长笑了:“没事的,都是一家人了,不客气。”
初到连队的第一餐很好,大米肉菜,大家饱餐后,没来得及溜达天就黑了,屋子里亮起了灯,由于各班都有了新兵,每个屋子里都有了欢乐的笑声,新老战士们正余兴未尽,就听见哨声响了,老高说:“熄灯时间到了,抓紧时间脱衣服,一会发电机就停了。”于是,战士们就抓紧时间脱衣服钻进了被窝。连队那边的发电机房里,一阵轰隆隆的很响,声音渐渐小了,电灯泡也由明转暗,最后完全灭了。
有人在被窝里趴着,打着手电筒在写家信,班长喊:“不要写了,抓紧时间休息。”那战士应着:“好了”一会儿,被窝里的弱光也没有了,屋子里一片漆黑。
又一会儿,屋子里就有人打起了鼾声,爱军惊奇他们的睡觉速度。许是不适应这新环境?许是看到的这军营与自己所想的格格不入?爱军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爱军做小学生时就有过从军梦,他家乡的小县城就在京广线上,离京广线不远就有一个军营,他曾绕着军营走过,高高的院墙里有一股神秘感,军营的正门,两边是荷枪实弹的卫兵,卫兵两边的墙上,写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一队队军人迈着整齐地队伍从大门里出来,向训练场走去,从大门外往里看,绿树掩映下,是排排的红砖红瓦房,里面配上穿绿军装的走动的军人,像是一幅靓丽的风景画。上初中那年的礼拜天,生产队派他拉着车子到军营里送过喂马的军草,到过他们屋里,那真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上下铺上,是豆腐块似的被子,鞋子、挎包,要放哪都放那,牙缸、牙刷也都排了队。一切那么地井然有序,令人向往。这一切更加坚定了他从军的欲望。今天,他穿上了军装,梦想实现了,可是,家乡的那座军营和眼前的军营竟是两个不一样的现实。尽管在新兵连他对铁道兵有了初步了解,但那依然是一个火热的军营,他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如今会来到这与世隔绝、荒凉的草原,会蜗居在这土堆房子里,就这么一个很小很小的、不能再小的军营里了,这么一个孤独的军营,就像一只孤雁,新兵连的那种火热的生活也不可能有了。他也没想到,这土墙上写的竟都是劳动的口号,什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什么以艰苦为荣、劳动为荣、当铁道兵光荣,等等,连一丝打仗的含义也没有。这还叫兵吗?想到这里,他似乎明白了新兵连的教育,铁道兵是工程部队性质,铁道兵就是修铁路,可是,为什么非要穿军装呢?答案有了,铁道兵走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有的是生命禁区,那么多的隧道要打,要牺牲要死人的,工程队干不了,要部队干吧,部队不怕牺牲。要想让边疆、少数民族、闭塞地区的老百姓尽快过上好日子,只能组建一支这样的部队,这大概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英明决策吧。。。。。。
还有,到了老部队,也该写信告诉家里地址了,不然,家里怎么联系呢?家里人会挂念,可这信怎么写呢?照实写,家里会更挂念,也会影响家乡人对自己的崇敬,究竟该怎么写呢?他想啊、想啊,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营房内外的漆黑连着草原,营区里两个不同方位的哨兵,背着挂刺刀的步枪来回游动,他们碰了头,吹了吹冰凉的手,跺了跺冰凉的脚,拉起了家常。眼下,虽已进入阳历四月,但在这极寒的北国,一米以下就是永久的冻土层,所以,尽管白天十分暖和,晚上依然寒冷。两个哨兵边说话边跺脚取暖,连里那条叫阿黄的大黄狗就蹲在旁边,陪着他们。这时,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狼的长嗥声,蹲着的阿黄一下子竖起了耳朵,警惕地望着草原的深处。一个战士说:到猪圈那边看看吧,不要叫狼把猪咬死。另一个战士说:不用,就拿起一个坷拉用劲向猪圈扔去,嘴里说了一声“去”,那阿黄就蹭蹭地跑了过去,绕着猪圈跑了一圈,就又小散步地跑了回来,在二人面前叽叽了两声,就又蹲下了。一个战士说:看看,我说没事吧?咱这伙计好着呢。



 河边草
河边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