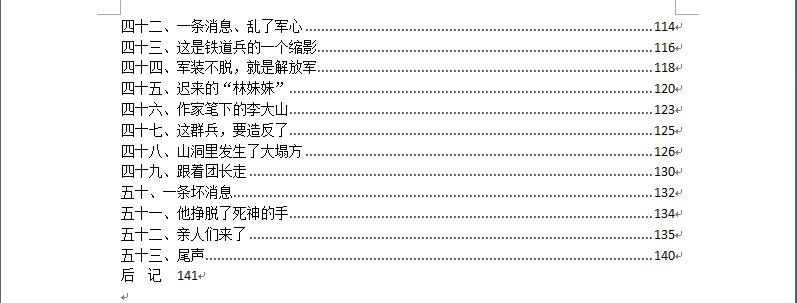十、铁道兵 ,是干活的兵
天亮了,嘟、嘟、嘟,一阵急促的哨声响起,爱军一个滚儿爬起来,拿出了新兵连的本事,三下五除二,就穿戴整齐,摸一下帽檐,不偏不斜,再摸摸领口,风领扣扣好,领章尖对尖。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院子里各排集合完毕。只见陈排长站在营房前的操场中央,四个排依次地向他那里报到,陈排长又统一整了队,向连长报告请示后,开始出操了。:“一、二、一,一、二、一。”队伍走外面的大圈,陈排长在里面走小圈。:“张三,脚步错了,换过来,一、二、一,一、二、一”。
伴随着步伐,口号声喊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队伍里,喊声震天,战士们使足了劲。近听,很有力量,远了听,那劲就小多了,因为草原很大,没有阻力,不像爱军他们在新兵连,大家一用劲喊口号,一会儿,山里就有个回音回来了。
队伍后面跟着跑的还有连长、指导员,还有个又黑又矮、背有点驼的汤排长,也是爱军这个排里的老排长。从前,在爱军的眼里,解放军都是很英俊的,现在,他也穿上了军装,军人也没那么神秘了,再仔细瞅,这军人里也有美丑好坏,就说这汤排长,若不是有一套人见人爱的军装罩着他,他就算个丑人,但是,这汤排长可是立过大功的,在修成昆铁路时,有一次隧道塌方,他冒着生命危险,一连往外背了五六个伤员,还往外背了几个死人,他那驼下去的背,就是干活时不要命累成那样的。
陈排长,不是,这是爱军新兵连叫的,老兵们仍然叫他陈排副,他还穿着两个口袋的士兵服,还没正式任命他为排长。那么,为什么出操汤排长不带队,要陈排副来带队呢?因为,汤排长就要退伍了,现在,他的老婆就在连队里的一个小土屋里住,专等汤排长手续办妥了和他一块走。这陈排副提干也是板上定钉钉的事,十拿九稳,所以,汤排长就把这应该做的工作交给了陈排副,他还要跟着陈排副到工地上走走,也叫扶上马,送一程吧。
军营生活紧张有序,一切都是按分钟计算,跑过操洗漱,紧接着就是开饭,炊事班的战士抬到院子里几篓子二米饭,战士们围上去一人干了一碗,回到屋里,坐在自己的铺边上吃。老高到炊事班端来了小半盆菜,一边喊:“来呀,吃吧,这菜又筋又绵,像肉的感觉。”一边拿着勺子给每个战士碗里打菜。菜不多,依然没有分完,爱军分到碗里一点儿,这什么菜?黑乎乎的,爱军仔细看:是用水泡开了、又用油炒熟了的多种压缩干菜,里面有干豆角、干菠菜,干白菜。这些都经过脱水处理,没有一点叶绿素,爱军吃了一口,像棉花、又像肉,除了盐味,什么味也没有,咽起来不好往肚里下。那就多吃米,可二米饭里高粱米太多,吃起来又苦又涩,大家一边吃,一边听孙玉生牢骚:“妈的,一顿干菜,一顿酸菜,闻着就有股尿骚味,这在我们家喂猪都不吃的。”有个北方兵说到:“难道你家每顿都炒几个菜不成?”那孙玉生把碗往铺上一放吹开了:“几个菜不容易?要做饭了,烧饭的女人往房前屋后一转,几个菜到手了,拿回来,蒸、煮、炒、拌,耶,耶。”孙玉生眯起了眼睛,嗅起了鼻子,众人都大笑起来。老高说:“喷吧、喷吧,照你这么说,你在家天天都吃上宴席了”班长和孙玉生是老乡,他认真地说:“孙猴子说的不假,有没有肉无所谓,不过,每顿饭几个菜是真的,只不过太远了,猴子,你就每天对着南边的家乡闻味吧。”大家又一次大笑。陈排副走过来:“猴子,吹吧,别人都吃过了,要上班了。”孙玉生赶紧扒拉了几口,碗里还有一点,顺手朝门外甩了出去:“去他娘的,留着肚子中午吃吧。”陈排副骂道:“妈的,在家就这样?浪费食物。”孙玉生嘿嘿地笑道:“习惯了,忘性大。”爱军看门外是一片白,拿起扫帚到门外扫了扫。
吃过饭后,连队通知:所有新兵到事务处领施工棉衣。因为这个地方无霜期很短,有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说法,所以,他们除了有施工单衣外,还发一套破的施工棉衣,这些破棉衣都穿了几任铁道兵了,有的棉衣上还写有退伍兵的名字,他们退伍时交上去,新兵来了,经过洗刷缝补,再发下去。这些衣服穿起来很随便,热了、脱下扔到一边,冷了就穿上,战士们戏称是离不开的火龙袍。
新兵们聚结在司务处门口,司务长叫一个名字,里面的上士就拿出一套棉衣递出来,不管大小,拿起来就走,有的干脆穿到身上就走了。爱军站在新兵的队伍里,前面一个是同班的小个子新兵,叫吴胜利,轮到他时,司务长上下打量了他一下,自言自语:“怎么小的个子,该不是不够年龄吧。”那小个子新兵嚷起来:“够的、够的,年龄小,报不上名字的。”小个子兵是广西人,普通话说不太好,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崩出来的。司务长对里面拿衣服的上士说:“找一套最小的。”里面一阵翻腾,就有一套棉衣递了出来,小个子兵穿上试了试,又肥又大,司务长眯着眼乐了:“你个小八路啊。”一时,众人哄堂大笑。司务长说:“将就着穿吧,没有合适的了。”及至小个子兵走了很远,司务长还在说:“哪个带兵的不长眼,把人家娃儿带来,受的了吗?”
司务长喊小个子兵叫小八路,听见的人不少,于是就传开了,后来,小八路就代替了他的吴胜利的真名。
衣服领齐,新兵们又上了材料库,领了铁锹、洋镐,回到班里,班长笑着对他们说:“武装齐了,这是咱铁道兵的三件宝:铁锹、洋镐、破棉袄,该有的都有了,准备上班吧。”
嘟、嘟、嘟------,值班的陈排副用力地吹着哨子,没有一分钟,他就把整个院子转了一圈。营区太小,这里用不着军号。
哗啦啦,从各个土房子里,走出来一群群身穿破旧军棉衣的人,爱军他们这些新兵也混在里面,此时,院子里再也分不清新兵老兵了。忽然,爱军在这群穿破棉衣的人中,看见了一个很面熟的小个子,这不就是新兵连那个柳眉细眼、快活的就像个百灵鸟一样的通讯员吗?今天,他和大家一样,穿的像个叫花子,他也看见了爱军,他向爱军做了个鬼脸,就入了他的班排的队伍里。
一会儿,这群穿破棉衣的人列好了队,四个排,依次向南边的铁路工地走去。
队伍刚走出不远,黝黑、结实的驼背排长跟了上来。
“老汤、老汤。”一个穿紫色大褂、留披肩发的漂亮女人,站在营房边喊:“你今天不是说上团部去吗?”汤排长边走边说:“改日吧,今天下游过来的顺路车太少了。再说,我到工地跟陈排副有些事要交代呢。”
“死老头子,你心里只有你的弟兄呐。”说吧,赌气的一回头,朝土屋里走去。
团部就在他们连队的上游,约有五六十华里,那里是一个有五六百牧民居住的小镇,一条五六百米长的土街上,有商店、邮电所,还有团部机关、汽车连,机械连,战士们就认为那是很热闹的地方了,有小香港之称,战士们最开心的事,也就是到团部转转。
汤排长还没有跟上来,队伍里就有了议论:“哎,汤司令(一个电影里敌军官的名字)老婆蛮漂亮啊!”“我们排长命好啊,你看,弯腰驼背的,这女人嫁给他真有点------”这话后面的词儿可能不好,那战士犹豫着,孙玉生倒是嘴快:“那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老高笑着说:“当心让汤司令听着。”孙玉生压低声音说:“听见了能给我咬掉了?”一边走着的陈排副听见了说:“说什么?大声点。”队伍里响起了嘻、嘻、嘻的笑声。
队伍有形,但步伐很乱,陈排副也穿着破棉袄,走在队伍一边的指挥位置上,只是不喊口号,其实,喊也没意思,一群穿破棉衣的人,肩上扛的是铁锹、洋镐,哪有一点军人的风度?他也听见了大家议论汤排长,只是他不想参与更多,因为有了汤排长的竭力举荐,才到了今天有可能提干的份上。
队伍走着、走着,有的排就改变了方向,去执行其他任务去了,说白了,就是干其他活去了。
队伍来到了一座靠近铁路路基的一架山下,汤排长和陈排副比划了一会儿,陈排副就喊:“十班、十一班,都上山吧,向山下翻石头。十二班,在山下的平台上装汽车,大家开始干吧。”
山坡很陡,大家迈着坚实的步子,踩着乱石, 一步一摇的上山,跟在大家屁股后面的孙玉生晃着身子说:“今天好熬些,沾了新兵的光,光是领衣服、领工具就耗去一个小时。”班长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月底完不成任务,是不会休息的。”孙玉生说:“得过且过,太阳底下暖和。过一天说一天。”
爱军气喘吁吁地和大家爬上了半山腰,这里是一个很大的石料场,满眼的石头犬牙交错,班长首当其冲,弯腰掀起一块石头,那石头就骨碌碌地向山下滚去,老兵们都这样干,爱军照样子也这样干。然而,爱军的家乡是平原,没干过石头活,也小看了它,他去掀一块较大的石头,自己这么高的个子,就该掀大的,他用足了劲,石头却纹丝不动,只有去掀小的。
石头你一块、我一块地往山下滚,山坡虽陡,却是坑坑洼洼,前面的石头一阻,后面就阻一大片,战士们就下去一层再翻,再下去一层翻,一直翻到山脚下的平台边,平台下站着拉片石的解放牌翻斗车,十二班的战士们,把石头掀到车上,把车砸的是咣当咣当的响,车装满了,那汽车哼着、摇晃着出去,开向有需要片石的工地,又有空车机灵咣当地退到平台下,继续装车。
铁道兵就是这样子啦?尽管这样的工作使爱军有些意外,尽管他从未干过这山里的石头活,可作为新兵,他并不想比别人差,现实就是这样的,只有义无反顾的走下去,否则,没有退路。
爱军一连几回地上、下,快走猛干,累的大汗淋漓,脸红扑扑的,他见晶晶坐在一块石头上喘息,笑着问:“怎么样?”晶晶擦一把汗,摇摇头:“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这个,我得想办法回去。”爱军笑笑:“这是部队,不是开店的,你以为你是谁?想走走?想来来?”晶晶叹一口气:“那就到年底退伍吧。”爱军说:“坚持吧,咋的也得干满三年。”“不、不、不。”晶晶连连摆手。
老高来到二人跟前:“累了?那就歇歇。”爱军说不累,晶晶并不吭声。老高又说:“一看你俩就是平原来的,山上的活没经验,这上山不能急,急了,心跳的厉害,很累人。”他指着从山下一步一摇地、上来的小八路说:“你看他,步子很稳,不慌张,也没你们汗多,也没你们脸红,一定是在山里长大的。”小八路上来了,老高问:“喂!在家干过这个?”小八路带着浓重的广西腔调说:“我们家是仙(山)多、西(石)头多,多见西(石)头少见人的啦。”说的大家都笑了。
爱军他们到了山上,又要翻下一批石头,老高用长兄的口味说:“慢点,你们掀小的,我掀大的,过个一年半载,身上有了力气就好了。”爱军听了,周身感到热乎乎的。
又一拨石头掀到了山下,和十二班的人和在了一起,人更多了,孙玉生突然登上了一块大石头,解开裤子,仰起脸,嘴里一边唱,一边掏出那东西就尿:
对面看见阿妹来,
不高不低好身材,
山歌一句扔过去,
看她理我不理睬
。。。。。。
众人嬉笑地观看着。班长笑着骂道:“妈的,不但耍流氓,还唱流氓歌。”孙玉生不以为然,依然神经的眯着眼唱。一旁的老高突然大声喊:“猴子,花姑娘来了。”孙玉生本能地一提裤子,弯着腰,手搭在额上,瞭望了一周,未见异常,回骂到:“妈的,害得我差点尿到裤子里。”众人又一阵大笑。孙玉生继续撒尿。
半晌已过,沉重的体力消耗、加上年轻人的消化特别好,再加上早饭的压缩干菜、二米饭都不愿意多吃,此时,已是饥肠辘辘,劳动效率自然低下,孙玉生有气无力地干着,忽然,他往地下一躺:“不行了、不行了,要昏死了。”大家没有理会,他的恶作剧也见的多了。
孙玉生躺了一阵,山下传来喊声:“喂,没有石头了。”班长吼起来:“猴子,还没躺够?”孙玉生一个鲤鱼打挺,蹭地坐起来,追着一块石头,一口气掀到了山下。老高喊道:“猴子,正常点,何必呢?”孙玉生说:“老子就这样,干是干,歇是歇。”老高说:“你这个样子,干的再多,上面也不会表扬你。”孙玉生说:“老子就这样,表扬不表扬,管屁用。”
快要下班了,班长喊:“老高、来钻几个炮眼”老高拖来风枪,接好风管,班长按住风枪就哒哒哒地钻起炮眼来,风枪扬起的尘土罩住了班长,一会就成了一个土人。
爱军这才看见了风枪的样子。也就是陈排长说的那风枪。
按说,在隧道里打风枪是要接水管的,那样粉尘小,对身体危害小,要知道,铁道兵有很多战士在隧道里打风枪得了矽肺病。但是,在这石料场打风枪,一是用时短,二是没有水源,所以,这水管就省了。
爱军以为自己人高马大,凑过来:“班长,我来。”班长说:“你不行,你时间还短,还不知道这风枪的脾气。”
嘟、嘟------,陈排副吹响了下班的哨子,难熬的一上午终于到头了。战士们开始收拢钢钎、大锤等工具,就下山了。班长和老高两个人,赶紧地把一管管炸药塞进打好的炮眼里,布好足够的引线,班长站在一块巨石上,把两手拢在嘴上:“喂!放炮了-----。”老高则挥起两面小红旗,朝山下各工点干活的战士们使劲的摇晃了几下,就一口气点燃了所有的炮,二人迅速地向山下跑去。
山下装车的平台上、路基上各施工点的战士们,在向安全地带移动,山上的战士们也跑的极快,他们大概习惯了,身子轻的像猴子,跳跃着一会就到了山下,爱军虽没有走过山路,但从农村摔打大了,又人高马大,虽然没有跌倒,但跑的也不慢。晶晶就不行了,在城里从没有走过孬路,山又陡,一听说放炮,跑起来就收不住脚,跌跌撞撞地摔了几次跤。新兵里数小八路跑的快,他人小身轻,一会就没有了踪影。
下得山来,点过炮的班长和老高也赶来了,“快点”班长喊。晶晶使劲地跑,只觉得脚下生风,但终赶不上队伍。前面孙玉生站住了,等到晶晶近前,拉住了晶晶的手。赶上来的老高也拉住了晶晶的另一只手。他们拼命地向前跑。
咚、咚-----,山上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腾空的巨烟像团团蘑菇,极为壮观。战士们无心欣赏,只顾着跑,就听见头上有鸟群飞过,抬头看,呀!炸起的石头,漫天都是,从后面越过了头顶。孙玉生拉着晶晶站住了,又喊爱军:“不要动,向天上看。”没有跑到安全地带的战士们都站住了,仰望着天上的落石,左躲右闪。石头就在战士们的前后左右扑嗒扑嗒地落下,新兵们看的可真是心惊肉跳。
炮停了,战士们到了一起,新兵们仍是惊魂未定。“吓死我了”晶晶说:“哪块石头砸中了你,都能要你的命。”孙玉生很平静的说:“这不怕,咱虽没到安全地带,但飞来的石头小了,少了,看准石头的着落点躲闪就是了。”又说:“看不见的石头最可怕,下游有个连队放炮,不知是装的药量过足,还是离连队太近,有个病号躺在帐篷里睡觉,被一块飞来的巨石击穿帐篷,落在身上,死了。”孙玉生说的轻巧,似乎这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晶晶听了,心底依然生起一股凉气。
战士们列队,无声无息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饥饿、乏力,使队伍没有了来时的活泼、乱语。孙玉生耸拉着的头一会歪向这边,一会又歪向那边。两脚好像擦着地面走,发出沙沙沙的声音,爱军饿的头懵眼黑,恨不得立刻回到连队,倘若此时有早起的压缩干菜、二米饭,也会毫不犹豫地吃上两碗。
中午开饭了,炊事班照例抬到院子里几篓子二米饭,战士们争先恐后地打满了碗,回到屋里,值日生老高端进来半盆香喷喷的黄豆炖豆腐,虽然不错,但豆腐也是黄豆做的,属同类,是炊事班自己磨制的,遗憾的是里面没有一根菜,主要原因是,驻地无霜期太短,种不出来菜。南方的菜也运不进来,而黄豆一年四季运输比较方便。
大家端着碗等着分菜,老高端着另一个盆又去了炊事班,说是菜不错,炊事班如果没分完,可以再加点。等急了,孙玉生说:“耍滑头,这有什么难事?我来分”新兵让老兵,老兵让上级,先给陈排副打、再给班长打,再给战士打,孙玉生心善,给谁也不愿意少分,快见底了,还有他和老高没有分,此时老高端着空盆一脸败兴地回来了:“妈的,眼见那么多的菜,说没有了”孙玉生也骂道:“妈的,老子替你分菜,连我的菜也没有了,你不要吃了。”老高往碗里倒些菜汤,说:“我不吃了,你吃吧。”陈排副见了,把自己的菜全拨给了老高、孙玉生,“妈的,炊事班不吃,也得给干活的吃。”说罢,拿起空碗,朝炊事班走去。
陈排副来到炊事班:“喂,怎么搞的,弟兄们累了一上午,孬好饭得叫吃饱阿,来,打一碗菜。”炊事班长赶紧赔笑,不敢得罪这位未来的排长,接过碗,很劲地弄了满满一碗,陈排副端着碗到了班里,与其他弟兄们又分了。
饥肠辘辘的战士们狼吞虎咽,一会儿便风扫残云地解决了问题。
吃饱了肚子,碗里晾了开水,困乏的战士们,有的坐着小凳子,趴在铺沿上挤着眼睛,有的挺着肚子,斜坐在小马扎上,头枕着铺沿养神。铺上的被子叠的像豆腐块,并且,一字排开地成一条线。这样的规矩,要一直保持到晚上睡觉时。
“喂,喝水,喝过了水打土坯去。”班长喊了起来,他一饮喝了自己碗里的水,拿起铁锹出去了。
连队的设施还未建好,现在在建三用堂,到了冬天学习、吃饭、演电影用。完全靠午休、工余时间干。
爱军喝了水,拖着酸痛的身子,拿了铁锹,随大家往外走。孙玉生猛地站起来,一拳砸在铺上:“妈的,劳改队。”由于用力过猛,碗里的水溅了一铺。老高附和着说:“是穿军装的劳改队。”
孙玉生见大家一个个都走了,也拿起铁锹,有气无力地跟了出去。其实,他就一张嘴,什么工作也没落下。
院子里一个排的人在垒土房子,有人在下面递土坯,有人在上面接了垒土坯,还有人推着人力车,从草原上源源不断地往这边运送土坯。爱军他们的班排就在远处的草原上打土坯。他们刨土,浇水,把割来的草和进泥里,用脚踩匀,班长拿一个木框子放在地上,战士们端来泥放进木框,班长手沾水抹平,一个土坯就成了。
这一个班就是一个战斗小组,这班长是兵头将尾,当得可不容易,各样的工作,不但要布置,还要冲锋在前。工作中,老高还可以,是连队唱歌的教员,文气、善良,只是劳动不占上风,所以想回去考音乐学院。其他老兵也可以,工作中要求进步,服从指挥。新兵们还不敢说,他们还没有过来劳动关,说多了,怕有思想问题。这最难管理的,就是自己的老乡孙猴子了,一有工作就是怪话连篇,你干多干少不说,落后话多了,能不影响大家?你看看,他来了,铁锨上挂了一点泥,耸拉着头,像吃了剩饭一样的有气无力,别人都端着满大铁锨的泥,越过了他,也全然不知。说轻了,跟你反驳,说重了,不搭理你。唉,走着瞧,讨论入团的时候再说,不投你的票,谁让你不配合老乡的工作?班长一边想,一边干,一个个漂亮的土坯从他手中出来,这些土坯再晒上几天,就可以垒房子了。
爱军强打精神,努力地干着,他想,那么多老兵都这样,自己也一定能闯过这个关,看看小八路,人小,却很能干,端着大铁锨的泥,身体却十分的敏捷,将来,工作上要是连小八路也比不过,那可就笑话了,这样想,身上也就有了劲。
班长看了看搁在一边的马蹄子闹钟,时间差不多了,就招呼大家洗手,准备上班。
回到班里,还没来得及喝口水,连队的上工哨子响了,又一群身穿破棉衣的人上路了,他们的工作,又是上午工作的复制。
吃过晚饭,新兵们都以为这一天过去了。错了,班长看看太阳还没有落山,就招呼大家拿上铁锨,撅头,到连队外面的草原上开荒。大家到了那地方,这块地很大,周围挖了沟,挖出来的土,在沟沿边上又堆了不高的围墙,地里又按排、班分成若干小块。这下可热闹了,连队一百多人都来了,横竖组成了很多劳动的人格子。
爱军和大家一字排开,有的用铁锨翻地,有的用撅头刨地,把草收拾成堆,到干了可以烧掉。他们再把土地匀平、整好,到季节了,再浇水、下种。副连长说了,到秋后,每人上交两千斤白菜。爱军心想,这么寒冷的地方,究竟能种成不能呢?但是,副连长说,算好账了,根据无霜期的天数,大白菜刚好能长成,人家守备部队试验成功了。
太阳落山了,大家扛着工具回去,爱军问:“这算一天了吧?”老高笑道:“不算,咱铁道兵有句话:两眼一挣,忙到熄灯,什么时候躺下了,才算呢。”这时候,孙玉生边走,边摇晃着身子唱了起来: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我们扛着铁锨归、铁锨归,
浑身累的酸又痛,
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
米搜啦抖擞----拉手蜜豆拉-----”
前面指导员在水井边洗衣服,老高捅一下孙玉生:“不要唱了”孙玉生不理会,继续唱。指导员搭话了:“小孙,编的不错啊,”
孙玉生笑道:“都是大实话。”
“编些好的,内容向上的。”
“不行啊,咱肚子里没有那东西。”
指导员笑了,指指脑子:“得装些好东西了,学习学习。”
“这鬼地方,有什么可学的?”
“解放军报、铁道兵报。”指导员说。
走过去,有人说,指导员不错,没批评猴子,还表扬呢。老高说:“政工干部就这样,婆婆妈妈的,没个肚量还行?”
回到班里屁股没坐稳,又一阵急促的哨声,紧急集合,大家赶紧脱去破衣服,换上了床头边的军装,整理领章、帽徽、武装带,只几分钟,一支雄壮的、和正规军一样的队伍就坐在了连部前的院子里。
只是这一支队伍太小了,也太孤独了,外面好像不知道这里有群人,大家互相盯着对方的三点红,才知道自己是军人。
指导员站到了队伍前面,文艺骨干老高领着大家唱了一曲铁道兵的兵歌: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唱过后,指导员说:“ 小高,教个新的,来个弯儿绕的好听的。”看起来老高早有准备:那就来个、人说山西好风光吧,自己唱了两遍、豆来米、豆来米,就一句一句教了起来:
人说山西好风光,
地肥水美五谷香,
左手一指太行山,
右手一指是吕梁,
。。。。。。
这对于唱惯了行进歌曲的部队来说,这歌曲虽然唱的没劲,但这调子确实优美好听,一股新鲜感暂时撵走了战士们的困乏。
教过歌曲,牛连长讲了当前的施工任务,副连长讲得最多,他管的就像一个杂货铺,管连队的副业生产,就是种菜,连队生活,包括磨豆腐,还有连队里养的猪,等。他特别讲了副业生产,他说:“经过走访当地的守备部队,经过测算当地的无霜期天数,在看看草原上这么肥的土质,我们一定能生产出很好的白菜,如果每人生产两千斤白菜,我们就可以不吃压缩干菜了。。。。。。”直讲的下面有人打起了瞌睡,军人的仪表失态了。
“喂,”牛连长大喊一声:“XXX,刚才讲的什么?”
那战士一下子醒了:“施工生产,保证完成任务,不能违犯纪律,有事请消假。”顺嘴流,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牛连长也笑了:“各班排回去,要总结一下前一段的工作,讨论一下今后的工作,还有副业生产,好了,各排带回。”
各排带回了,汤排长和陈排副又讲了排里的工作,讲了怎样落实连队布置的各项任务。回到班里,又开班务会,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敦实的黑脸班长讲着讲着,就有些忍不住了:“有些老同志,老卡卡的,不能以身作则,工作有气无力,尽说消极话,你给新兵树立了怎样的榜样?要注意,你是老兵了,要注意影响。”班长的话音刚落,孙玉生就撵了上去:“谁老卡卡的,老子少干了?干这鸟活、吃这鸟饭,老子发几句牢骚成事了?”班长反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论事不论人,又没提你名。”孙玉生说:“不是说我说谁?老子就这样,爱咋的就咋的。”班长说:“我倒是说错了?你倒是有理了?不接受批评,迟早会吃亏的。”旁听的陈排副吼开了:“猴子,还有完没完?大家可都是向着你呢,到现在,团都没有入,也不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
陈排副一顿很话,会议立即哑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事也只有陈排副来压台了,因为此时,汤排长已回到小土屋里与妻子温情去了。
其实,班长与孙玉生顶嘴不止一次了,孙玉生好发牢骚,班长以为他说消极话,撤自己的台,又因为是老乡,又因为很多事,又因为孙玉生的有口无心,他们又很快和好,所以,说他们是狗皮袜子没反正。
嘟嘟----嘟嘟----熄灯的哨子响了。以上说了,这小军营用不着军号,哨子一吹全听见了。
班务会不欢而散,大家默默地、急三火四地洗脸、洗脚,赶紧钻进被窝,一会儿,连队里的发电机熄火了,营区一片黑暗,疲劳、困乏,阵阵袭来,使你想不了多少,一会儿,屋里就传来了战士们的打鼾声,好好睡吧,明天比今天的工作,有过之而不及,劳累、枯燥,充满险数,但你必须前行。



 河边草
河边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