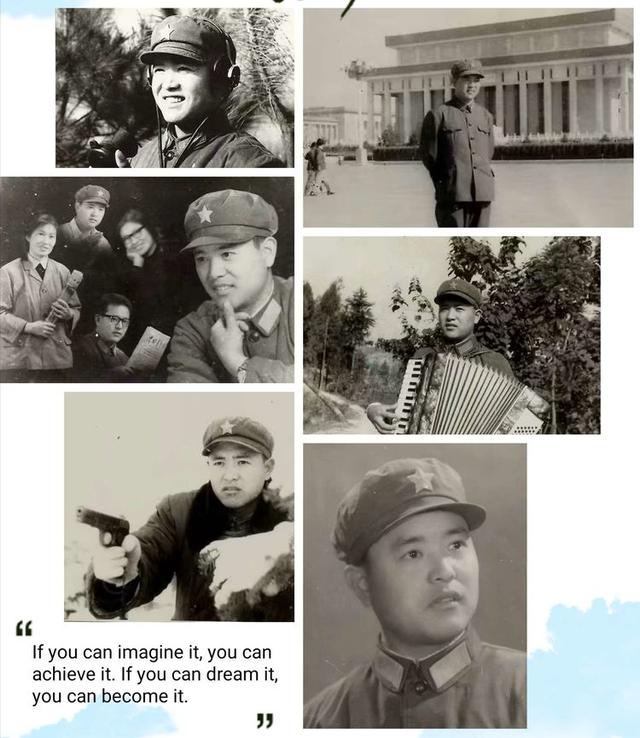记叙文 陝南往事 (二)
文/原铁道兵52团勤务连 杨玉恒
(二) 汉江老船工
当年我们部队驻在安康岚河口的时候,我结识了一位常年在汉江边岚河口摆渡的老船工,老人六十左右岁,中等身材,黝黑的脸庞,刀刻般的皱纹,络腮胡须,身体还算硬朗,也许是常年累月在江边摆渡的原因,两腿患有静脉曲张和关节炎,走起路来有点瘸。
因为我经常搭乘他的渡船到汉江对岸给部队修理电话机和总机,所以久而久之便和老人逐渐熟悉并成了朋友,也对老人有了一些了解。

老人无儿无女是个五保户,为人朴实、正直、脾气有些暴躁,喜欢喝酒,有时晚上喝醉了酒就坐在船上骂,而且骂声传得很远,汉江两岸都能听得见,但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骂,更不知道他在骂谁。
也许老人是用这种民间最古老、最通俗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苦闷,也许人们鉴于对老人的了解和同情而习以为常,所以没有人去理会,也没有人去劝解,如同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平常;又似乎是在情理之中的自然现象。
第二天醒来,老人依旧当着他的“船长”,依旧“吆五喝六”地指挥他的乘客,而且会对那些不听指挥的乘客大声训斥,偶尔还要骂上两句。我就曾经被他骂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那是一九七零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在连队刚吃过午饭,由岚河口邮电支局转来电话说,驻扎在汉江南岸的团部卫生队(部队医院)一台十门电话总机坏了急需修理,我立刻带上工具包急急忙忙赶到了岚河口渡口准备过江。

但是非常不巧,此时的渡船是停靠在汉江南岸没法渡江,我心里非常着急,于是,我立刻跑到江边的一个高处,捧起两手作喇叭状向对岸大声喊叫:“啊——太公(当地对船老大的尊称)”“啊——太公”,但对岸没有应声,我又连喊了几次后,才看见老船工慢慢悠悠的站起身来大声问道:“喊啥尼嘛?”我连忙回答:“过河呢!”“啊,等一哈儿”。
但我发现老船工并没有表现出马上要摆渡的迹象,却又慢慢地蹲下了,我心里那个急呀,想再喊几声又觉得催急了不好,只好再等。又等了好大一会儿,才看见老船工和一个过江的人把船从汉江北岸划了过来。我心里明白,只是着急得有些糊涂了,渡船只有人掌舵而没人划桨能行吗,何况中午过江的人本来就少,所以,老船工只能等到有人过江才能够把船划过来。
老人的这条船约有十米多长,一米多宽,船头为头桨,船中部为二桨,船内有几道隔板,最后是船舵。平日里,过江人多的时候可由两个人划一个船桨。
渡船离岸后,老船工先让我划的是头桨。因为那时部队刚到岚河口,我又是北方人,从来就没有划过船,也不知道该怎么划,只好硬着头皮按照老船工的交待开始划头桨。
当渡船划到江心时,老船工突然又让我改划二桨,我连忙跳过隔板再去划二桨。当时真是手忙脚乱,船桨也不听使喚,老船工一见此景发火了,大声地呵斥我:“松蛋,干啥吃尼吗?!”更可气的是,他还不断地大喊大叫:”船溜了!船溜了!”“干哈尼嘛!用力搪吆!用力搪吆!”“船溜了!船溜了!”......
所以,我对他的这种呵斥和大呼小叫非常反感,也很恼火。心里想,若不是我急于过江去修总机,才懒得理你呢!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总算把船划到了对岸。

我带气把竹篙从船头那个孔里插到岸边沙子里定住船,放好下船的木板,把铁锚拖到岸上用脚使劲踩了踩,然后招呼也没打,径自向卫生队走去。我爬上岸边一个高坡后无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只见老船工面朝江面,背靠舵轴,左手扶着舵把,一声不吭的坐在那里抽着他的旱烟袋在发愣。
当我修好了总机回到船上,老船工口气软软地向我解释了他刚才发火的真正原因,看来老人已经看出我生他气了。
原来,行船的人最忌讳的是船到江心舵桨配合不好,因为江心水流最急、最深、最危险,一旦船桨和船舵没有配合好,让船横在了江心,急流就会把船掀翻,后果可想而知。我一听这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里也在狠狠地责备着自己,反思着自己今天对老人态度确实有点过分了,我应该感谢他才对啊!

由于那次过江得到了经验教训,此后再乘坐他的渡船,即便老人再发脾气,再大喊大叫(或许这就是船工们的一个职业习惯),我也能理解了。
当然,此后他再也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以后无论何时有事过江,只要报上姓名,我们总能配合默契地安全渡过江去。再后来我还与老人成了朋友,在船上还喝过他煮的“苞谷青菜糊糊”(玉米菜粥)呢!
岁月随同汉江水,转眼流逝几十年。或许老人早已辞世,但他的音容笑貌和他走路一瘸一拐的身影,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难忘......
整理:尤兴益
责编:严京平《白浪情》



 河边草
河边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