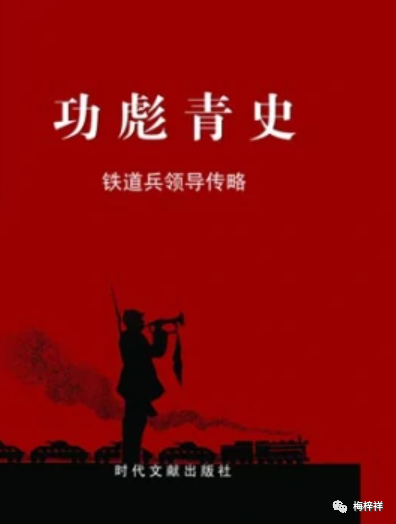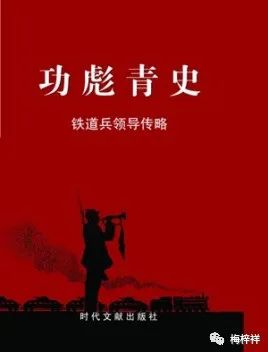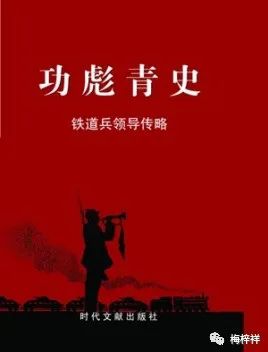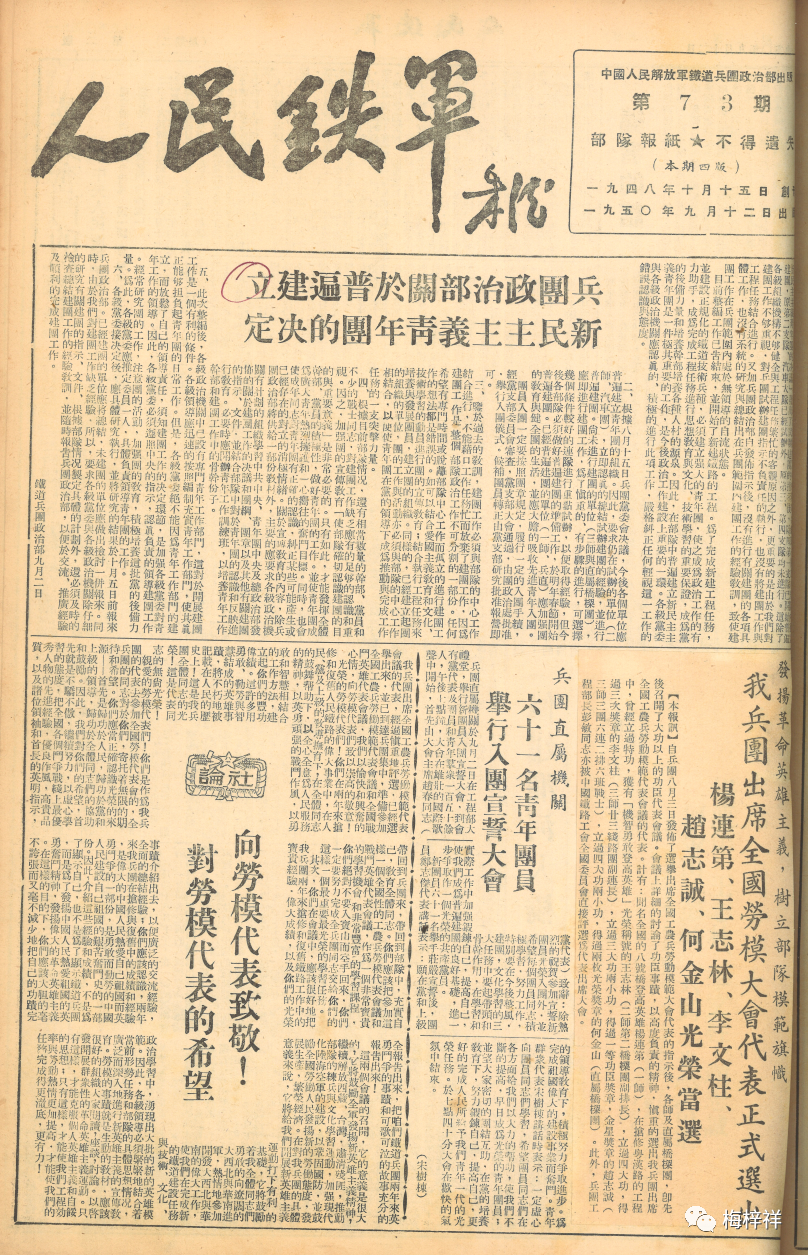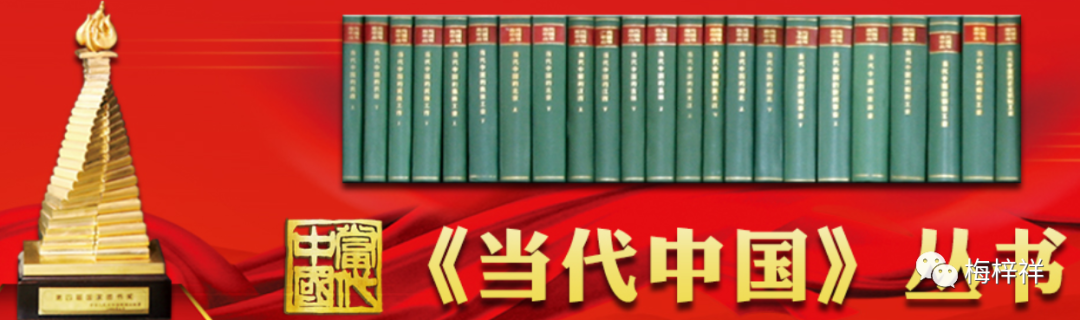七、家和人亦和
黄荣森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父亲黄业田1956年因病去世时,挨肩的三个妹妹,最大的只有五岁,最小的不足一岁。母亲陈箐慧是农村妇女,性格温存,贤惠、善良,丈夫过世后,家庭生活时常陷入困境,然而她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有。
黄荣森在部队享受供给制,每月只有很少的津贴,为了帮助母亲养家,他平时注意节省每一分钱。提干后,更是每月都给家里寄钱、寄粮票,毫不夸张地说,三个妹妹是他帮助养大的。
黄荣森、崔木兰结婚照。
1956年,黄荣森与相识多年的同邑好友、某部队文化教员崔木兰结婚。崔木兰1951年入伍,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内蒙古乌兰浩特实验小学当老师,带着两个孩子与黄荣森两地分居,不幸的是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患帕金森氏病。
帕金森氏病又称震颤麻痹,是一种影响患者活动能力的中枢神经系统慢性疾病,患者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如穿衣、脱鞋,洗漱都感到困难。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种病无法根治,只能靠药物维持。
1972年秋,崔木兰跟随丈夫到兴隆时症状非常严重,那时国内尚无特效药,北京刚刚能买到国外进口的“左旋多巴”。然“左旋多巴”这种西药治标不治本,长期服用后药物的时效便逐渐缩短,且副作用很大。北京有个门诊部自制中药“消颤丸”,副作用小,且有一定疗效,但需自费。黄荣森经常去北京为妻子买药,不能亲自去时便托人帮助捎来。
自从妻子患病,黄荣森一刻都没有离开过她,穿脱衣服、鞋子,洗脸、洗澡,喂药、喂饭,剪指甲、做饭等都亲力亲为。我去黄荣森家串门,令我十分惊异的是他把自己的家收拾得洁净、素雅、温馨,将几乎失去生活能力的妻子侍候得让人根本看不出是个病人。我由衷地感叹:他是用一生来实践自己“爱的誓言”啊!
李志吉感慨地说:“崔阿姨的双手整天都颤抖得厉害,行动受到很大影响。久病脾气就不好,阿姨常常对黄干事发脾气,但我从来没见过黄干事对崔阿姨发脾气。他对待爱人的态度,让我在感动的同时又深受教育。多年以后,我在照顾我生病的媳妇时,有时会想到黄干事伺候崔阿姨……”
世事无常,人间有爱。
黄荣森自携病妻调入六四四四工厂后,受到厂领导的悉心关照和同事们的鼎力相助。
追忆往事,黄霄川满怀深情,感慨万千:父亲与宣传队员们的友情似陈年的烧酒,越陈越香。他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赋予了这支业余宣传队辉煌,而队员们则给他带来了人间的真情和温暖。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每逢周末晚上,屋子里便充满了欢声笑语——这些远离父母的少男少女齐聚我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宛如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郭庆生无论是在政治处还是后来提拔为厂党委副书记,都是父亲工作中最贴心的搭档,两个人配合默契,把兴隆厂的政治宣传和业余生活搞得有声有色。郭庆生真挚地说,我有幸与黄荣森一起工作多年,耳濡目染其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终生受益。
李志吉在谈到黄荣森和宣传队员们的关系时说:“宣传队员们十分钦佩黄干事的工作能力,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从黄干事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受益匪浅。黄干事为人和善,平易近人,工作中非常有耐心,从不发脾气,与大家关系极其融洽。厂里不少职工羡慕这个特殊团队团结欢乐的氛围,调侃笑称厂宣传队是‘黄家协会’。”
退休后的黄荣森回归家庭,生活平静,每天主要的任务是照顾老伴儿,闲暇时便挥毫泼墨,练习书法。
黄荣森书法作品“”清心寡欲 ”,甲戌春月六十寿题。
1995年我重返第二故乡围场,返津时路过承德,在旅馆见到久违的工友曹建平等人。曹建平说工厂已迁址秦皇岛,估计再有一年将全部搬迁完毕。我当即提议“十一”假期在兴隆举办一次大聚会,邀请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老同事回厂叙旧。
此事商定后,我便给黄荣森写了一封信,告知会议议程,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我当时不知道他已退休,组织大规模活动有一定困难,然而他在回电中热情地一口答应,并将赴会人员的聚餐、住宿、联欢、会议等活动安排得妥妥帖帖。
1995年10月3日,一百多名从北京、天津、承德以及全国各地返回兴隆的老同事受到厂里热烈欢迎。一进厂区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人多高的大标语牌,上面用浑厚有力的红色颜体字书写着:“热烈欢迎老战友回厂团聚。”厂里的职工一般习惯称“工友”,很少称“战友”,一看便知这是黄荣森的杰作。他用醒目的标语烘托气氛,让久别而归的老工友感到亲切、温馨,一股暖流遍及全身……
1995年10月3日,铁道兵六四四四工厂部分职工在兴隆原厂址聚会。三排右起12人为黄荣森。前排右起10人为李小芹。
1996年黄荣森跟随六四四四工厂举家迁往秦皇岛。走出山沟,进入海滨城市,生活方便、惬意,老两口相依为命,黄荣森每天专心致志地照顾老伴儿的饮食起居。他在2003年9月22日写给梅梓祥的信中谈到自己晚年生活时说:
“我自幼偏爱地理课,人老了,自己房间里少不了的布置——就是挂张大地图。我常常凝视着地图浮想联翩,似乎在图上看到新时代的战友们正驾驶着现代化的筑路机械,在祖国的锦绣山河上‘织’着灿烂夺目的高科技铁路网……”
黄荣森绘制的“我到过的地方与途径路线”地图。
2005年崔木兰因病不幸离世。黄荣森多半辈子有规律地照料病妻,已成为一种惯性,如今戛然而止,使他精神恍惚。白天,他一个人守着空落落的房间无所事事,有时到了某个时刻,还会下意识地去给妻子拿药,说:“该吃药了!”然而环顾四周,屋子里静悄悄的,再无人回应……痛失爱妻后,黄荣森逐渐变得沉默寡言,即便在儿子的催促下到院子里晒太阳,也是独自坐在一边,远远地望着那些打牌、嬉笑的人们。虽然此后他回到久别的故乡济南,与弟弟、妹妹们共同生活了半年,但依然走不出孤寂的阴影,身体每况愈下。
李志吉无限伤感地说:“2016年秋天,我们铁后宣传队和厂宣传队一行十人去秦皇岛看他。他见到大家非常高兴。那会儿他脑子还清楚,分别多年,多数人的名字他还记得。黄干事的儿子霄川给我们照了合影。合影中的黄干事看上去笑意淘淘,满脸慈祥的样子,依稀还能看到他年轻时的神采。转过年,霄川告诉我,老爷子已经卧床不起,记忆力也衰退得厉害,基本不认人了。唉,最是人间留不住,容颜辞镜花辞树。人为什么要老呢?不过,在我心目中,那个卧床不起的耄耋老头儿,永远是那个满腹才华,做事细致入微,对我如师如父的黄干事!”
2016年,黄荣森与儿子黄霄川摄于秦皇岛。
黄霄川说:“父亲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家属和子女,从不徇私舞弊,搞特殊化,一辈子不愿意求人,任何事皆顺其自然。我十五岁进厂当车工,一干就是十八年,随着年龄增长,经常犯腰痛病,我想让父亲找领导帮助调换工种,但父亲始终不理睬,好像会犯多大错误似的。直到腰部疾患愈来愈严重,我自己找领导提出申请,才被调到检验班。”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不正之风便伴随而来。父亲的思想始终与‘潮流’格格不入,对于请客送礼等很多事情看不惯。例如,工厂受地形限制,只能收看河北省电视台一套节目,为了让职工同时能收看五套电视节目,拟安装卫星天线。1988年1月,上海的工程师带队来厂洽谈,父亲把价格压得很低,工程师说送他一张电视机票,被他断然拒绝,告知电视机票如果价值300元,天线的价格就再降300元。”
说起父亲一辈子刚直不阿、眼里揉不下沙子的脾气,黄霄川还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家住平房时,一天晚上八点多钟,父亲去位于山脚下的公厕如厕后回家,看见一个人扛着东西沿小路上山,立刻意识到这是有人盗窃厂里的原材料正在往厂外运,于是冲进家门大声说:‘有情况!’拉起我就往外跑。”
“我跟在父亲身后尾随着忽隐忽现的黑影爬上山。当时山上的庄稼已近一人高,窃贼发现我们在追赶他,走一段路便蹲在地里躲一躲。我们在明处,窃贼在暗处,追出很远还没有追上,累得我呼呼直喘,感觉实在跑不动了,便停下来。其实我心里选择放弃还有一个原因:父亲回家叫我时,我恰巧在试穿一双同事从天津捎来的新皮鞋,价格不菲的皮鞋踩着山上的碎石和杂草灌木,可把我心疼坏了,我劝父亲不要再管闲事。”
“父亲见我不追了,压低声音批评道:‘这就跟打仗一样,你怎么能临阵脱逃呢!’由于我耽误了时间,窃贼趁机逃脱。父亲气得鼓鼓的,回到家冲我大发脾气,狠狠地教训我整整一个晚上,说我贻误战机,是战场上的逃兵……后来没过几天,我家养的七八只快下蛋的母鸡全丢了。”
黄荣森正是以这样的优秀品德为两名子女树立了好榜样——儿子黄霄川,子继父业,勤奋工作,多次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荣立三等功一次;他亦是优秀共青团员、新长征突击手,厂里唯一荣获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管理部所属工厂“先进青年”称号的共青团员,将人生三十多年的黄金岁月贡献给了祖国的军工事业。女儿黄霄音,刻苦读书,女承母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
尾 声
黄荣森很早就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决定:一是捐献角膜,二是不留骨灰。
黄霄川说,“2021年5月17日上午八点,我喂父亲吃完早餐,他像往常一样坐在椅子上休息,不一会儿,我见他低下了头,走到近前,才发现他竟然已驾鹤西去,平静安详地走完了八十七年的人生之路。父亲一生谦和、低调,他生前遗愿: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捐献眼角膜;骨灰一半撒在爱妻坟茔,一半撒于故乡的黄河……”
黄荣森少小离家,故乡始终是他魂牵梦绕、牵肠挂肚的地方——那里有他的亲人,有童年和少年时的伙伴,有熟悉的乡音,有温馨的回忆……1955年8月2日,济南日报刊登了他写的一篇诗歌《战士寄故乡》,诗中写道:
“黎明,我走上山岗,在芭蕉树下眺望海上的曙光,浪花滚卷着奔向天边,士兵的心啊,飞回了故乡……谁都热爱伟大的祖国,但更怀念自己出生的地方。……”
七十一年前,他为了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复兴,抛家舍业,南征北战,然而无论走到哪里,家乡始终像风筝线系着他这个漂泊在外的游子。
黄霄川说:“父亲虽然生不能在故乡终老,我们遵照他的遗愿,死后‘落叶归根’。5月19日下午,亲属们将父亲的骨灰撒入了‘黄河母亲’的怀抱……”
梅梓祥在悼念文章中写道:
“获悉黄荣森病故,中国铁建铁道兵纪念馆向黄荣森亲属致唁电,髙度评价黄老以及创作的歌曲,是‘中国铁建宝贵的精神财富 ’。铁道兵文化公益基金张楚然,贵州、云南等省铁道兵文化联谊会等个人和团体,纷纷撰文悼念。铁道兵文化网、铁道兵战友网,永远铁道兵写作群、铁道兵快乐写作群等媒体,即时征集诗文,滚动发布。铁道兵微信群,文字、视频,花圈、烛光及符号,持续更新,数以万计,空前绝后。今日头条、新华网等媒体,也热情赞扬黄老及‘兵歌’。我在朋友圈转发介绍黄老的文章,点赞与‘双手合十 ’符号创历史纪录。中国铁建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李国瑞留言,表达了铁道兵战友与铁建员工的共同心声:黄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要不愧当过志愿军,
干啥也按志愿军的样子去做,
永远当祖国最可爱的人,
让我的金色和平鸽旁,
开满新的胜利花朵。”
这是黄荣森从朝鲜回国后,在《金色的和平鸽》这首诗中对自己今后人生的定位,也是他一生的追求和做人准则。难能可贵的是,他表里如一,说到做到,几十年革命生涯,他像当年的志愿军一样,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践行了“永远当祖国最可爱的人”的承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黄荣森的传世之作《铁道兵志在四方》将永远激励铁路建设者所向披靡!
(连载完)



 河边草
河边草